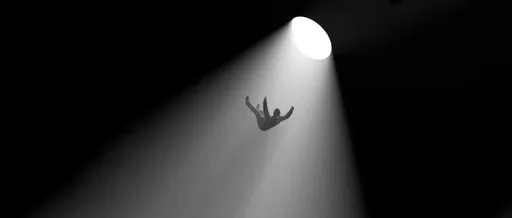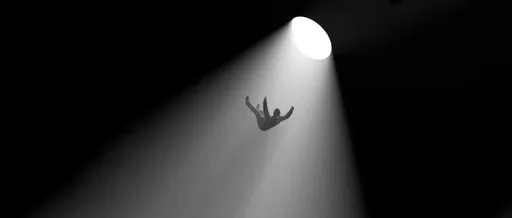谈论“哲学危机”本身是现代哲学的一个突出现象。西方哲学危机与现代性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标志现代性思维特征的一系列二元分裂,核心是人与世界的分裂,导致古代万物一体的世界观的终结,也导致以对宇宙和世界整体性理解为目标的哲学的日渐式微。失去了其本质的追求,是哲学遭遇危机的根本原因。哲学危机导致哲学日益脱离现实生活,成为孤芳自赏的纯粹理论;导致道德哲学缺乏真正的普遍性基础。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病的治疗不是要抛弃哲学,而是要纠正现代性传统对哲学的错误定位。
现代哲学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哲学危机不但成为一个不断被人们谈论的话题,而且也实实在在地在人们的生活中发生。一方面是哲学越来越成为学术工业的从业者们自娱自乐、博取名利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哲学普遍被人忽视,即使是在社会文化中也日益退居边缘的地位。普通人最多对成为一种文化消费品的伪哲学有点兴趣,但更多的则是对哲学敬而远之。
与此同时,也不断有人对哲学危机提出自己的种种看法。然而,这些看法往往是从外在经验层面的哲学不景气和日益没落来看哲学的危机,很少对哲学危机的内涵及其原因有所揭示。对经验事物的危机尚且不能仅仅通过描述其外在表现来把握它,对哲学危机就更不能停留在表面,因为那将无法认识哲学危机所包含的重大哲学问题,从而把握危机大多会蕴含的契机。
危机意味着严重的不正常,甚至不正常到要威胁事物本身的存在。因此,要知道一事物的危机究竟为何,首先要知道它一般是什么。哲学与人的思维有关。人的思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与我们的生存本能有关,以思考和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种种特殊的、现实的、实用的、具体的、个别的问题为目的。另一种则不然,它并不以任何具体、特殊的问题为目标,而以把握作为整体的存在为目的。哲学就是这种类型思维的产物,哲学的诞生是以人类试图从总体上把握大全()或作为整体的存在开始的。《易经》之所以为群经之首,就是因为它明确试图用“易”(不易、变易、易简)这个概念来从整体上把握天地万有的根本。而爱奥尼亚学派的哲学家用水、无限或气来解释世界存在时,也是这个意思。
哲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思考大全为根本特征。当然,这决不是说哲学不思考其他问题,而是说,哲学思考任何问题,都必然是在大全或作为全体的存在的基础上进行的,都必然可以还原为此一问题,因为大全问题不能肤浅地理解为纯粹范围问题,而应理解为最高的问题和终极性问题。胡塞尔说哲学从古代到近代都是“关于存在者全体的学问”,①不但符合西方哲学的事实,对于中国哲学也一样适用。
但是,哲学对此最高问题和终极性问题的思考,绝不同于一般的对客观知识的追求,而是要找到足以给自己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以根本指导的原则,发现自己和世界的存在根据,也就是根本道理,以使自己能够安身立命。没有这样的根本原则和根本道理,人类就会觉得自己无家可归,自己的存在是无根的存在。人与其他生物最根本的区别,大概就在于要给自己的存在找出一个理由,要赋予自己的人生以某种意义。但是,这种意义总是建立在人对自己和宇宙存在的理解基础上的,否则他就无法根据这种理解,而不仅仅是本能来决定他在世界上的种种行动。人在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的同时,也在思考世界和宇宙的意义,因为他一开始便把自己与宇宙视为一体。古人所说“为天地立心”,正此之谓也。
然而,哲学的这个特性,近代以来却被逐渐否定和抛弃。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现代性使然。胡塞尔曾明确揭示过现代性与哲学危机之间的内在关系。首先是万物一体的信念在近代动摇了,“这绝不仅是由于表面上的原因,即形而上学不断失败与实证科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成就锐势不减地越来越巨大的增长之间荒谬的令人惊恐的鲜明对比”,②而是近代科学(伽利略)将自然数学化,使得自然成为一个自身封闭的物体世界。这“很快就引起了关于世界一般的理念的完全改变。世界可以说分裂成为两个世界:自然和心灵的世界”。③
与此同时,是主体概念的出现,事实上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相关的方面。近代主体性概念是人对自己认识世界能力产生怀疑的产物,笛卡尔主体哲学的基本特征就是疑字当头。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笛卡尔哲学为两个噩梦所苦:一是实在性的噩梦,即无法确定世界的实在性和人类生活的实在性;二是对人的认识能力怀疑的噩梦。④这种最终只能确定自己的主体地位的主体概念,最终的结论是我们认识的不是世界本身,而是我们对世界的主观建构。
由此,近代西方的自然观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之大使得人们有理由把它看成是“重构世界”。⑤自然经历了从神的任意产物,到异教的命运女神,再到运动中的物质这样一个一再重新理解的过程,⑥自然最终被看作是一个独立于人的意志的机械物质运动的实体,只有内在的机械规律,没有内在的目的。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从属于自然的机械规律。笛卡尔和霍布斯在许多问题上有严重分歧,但在物质机械自然观和人从属于自然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培根、笛卡尔、霍布斯等思想家寻求一种新的开端,不再把人或神置于优先地位,而是把自然置于优先地位,试图不把世界理解为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的自由的产物,或者一个彻底全能的神的意志的产物,而是理解成物质的机械运动的产物。”⑦物质自然具有存在者层次上的优先性,唯物论与自然实在论成为最为流行的存在论理论。
但是,无论是伽利略还是笛卡尔,都认为物质运动可以还原为数学公式,自然界是“一部由时空中的物质运动所构成的巨大而自足的数学机器”。⑧世界是一个几何学的世界,“只能通过纯粹数学来认识”。⑨然而,数学认识的不是世界本身,而是数学化的世界,即我们人通过数学构造的世界。这样,“笛卡尔针对普遍怀疑获得确定性的方法,与从新物理学中得出的明显结论高度一致:即使一个人不能按照某物给予或揭示的样子来认识真理,他至少也认识他自己制造的东西。”⑩现在,理性是我们认识的最高权威,但这个最高权威所蕴涵的秩序,不是由我们心灵发现的事物的秩序,而是我们心灵构造的秩序。(11)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其实不过是以先验哲学的方式系统阐明和论证此一结论。
自然既然成了客体,成了对象,用理智与意志掌控这个对象、改造这个对象以满足人的需求,就势在必行了。要掌控和改造自然,首先要认识自然,认识论在近代的兴起,肯定与此有关。另外,掌控和改造自然离不开方法,从笛卡尔的普遍数学的理想开始,近代人一直对方法情有独钟,数学方法与逻辑方法成了科学和科学方法的代名词。当人把自然和世界作为自己控制和改造的对象时,他实际如柯瓦雷所说:“在世界中失去了他的位置,或者更确切地说,人类失去了他生活于其中、并以之为思考对象的世界。”(12)西方人也把世界离人而去叫做世界的异化。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理解也改变了人对时间的理解。在古代,西方人把时间理解为万事万物依据循环的自然秩序的生灭变化,时间意味着存亡兴衰,谁都不能逃避这个时间的法则。(13)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的时间是天启时间,过去的堕落与将来的救赎都已神定,这个时间与人的活动无关。但到了近代,随着人对自然界越来越大的征服和改造,历史开始被视为人类的进步史,有一定的方向和目标。这目标就是征服自然,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建立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可以自由地追求他们想要的一切,过舒适的生活。“这种进步的历史观是现代所固有的,是现代自我理解的本质要素。”(14)另一方面,随着把世界和自然理解为与人对立的客体,均一、虚空的物理学的时间观念成为标准的时间观念,这就“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但有时又显然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们如何将我们的生活与这种时间相关。”(15)
总之,标志着现代世界的,是一系列的二元分裂:人与自然、自我与非我、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自然的非社会化和社会的非自然化、自然与人文、教化与政治、精神与物质。不仅世界是分裂的,人本身也是分裂的:作为主体(意识)的人和作为客体(肉体)的人、作为认识者的人和作为行动者的人。人的能力也是分裂的: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信仰与知识、判断力与想象力、认识与审美、理论与实践、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人的生活也是分裂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总之,古代世界观和生活的那种统一的整体性完全消失了。而这种根本分裂的根源,是现代的特产——主体性原则。“主体性原则不但使理性本身,还使‘整个生活关系的系统’陷于分裂状态。”(16)这是黑格尔对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诊断。这种分裂使得哲学本身“经受了一种内在的解体”,(17)“‘最高的和终极的问题’统统丢弃了”。(18)
这样的一种分裂,还使得哲学不再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而成为一种狭义的纯粹理论。
康德在其哲学百科全书的课中告诉我们,古代哲学家把人的使命与实现此使命的手段视为他们科学研究(即哲学)的主要对象,直到近代,它们一直是哲学家的真实理念。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首次区分了思辨和智慧,认为思辨对实现人的使命毫无助益。他的哲学就是要教人智慧。古代哲学家都是智慧的教师,他们自己就如他们所教的那样生活。但是到了近代,人们把哲学看作是一门思辨的科学,它的任务不是让我们变得更好,而是教我们更好地判断。像哲学所教导的那样生活者,会被看作是在白日做梦。(19)
虽然希腊哲学家大多知行合一,能够像哲人那样来生活,但希腊哲学的主流倾向却是逐渐将理论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虽然人们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了人间,但苏格拉底感兴趣的却是定义概念和指出人们论证的错误;他自己的确以哲学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他的哲学却明显以理论为旨归。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理论生活方式视为最高的实践方式时,他们不过是把苏格拉底哲学中潜在的倾向加以突出和阐明而已。柏拉图虽然提出“哲学王”的概念,但在他那里,哲学家从政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一种牺牲。西方语言中“理论”一词来自古希腊文theorein(旁观),该词原意是指旁观、观看公众节日。这种公众节日的旁观者叫theoros,只看而不参与。进行理论沉思者是日常生活的旁观者,他们以沉思根本真理为职志。
到了近代,哲学日益成为纯粹理论,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两个转向——认识论转向和语言学转向,使得哲学越来越远离现实生活而成为纯粹的理论活动。康德在第一批判中特意区分学院哲学和世界哲学两个概念,指出世界概念的哲学与每个人都必然感兴趣的问题,即人的使命有关,(20)为此,他将实践理性置于理论理性之前,却无法避免他自己的哲学成为近代理论哲学或哲学理论化的典型,这正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同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哲学越来越理论化和“专业化”的结果,是哲学的功能范围日趋萎缩:“哲学剩下能做的,是解释性地沟通专家知识和日常实践的取向要求。留给它的是阐明并促进生活世界整体关联的自我理解进程。”(21)哲学的地位与合法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哲学本身陷入存在与否的根本危机,哲学死亡的判决书层出不穷。(22)即使以哲学家自居者,如哈贝马斯,也认为哲学“作为解释者也不能吹嘘与科学、道德或艺术相比,唯有它能洞察本质,它只拥有可错的知识”。(23)据此,哈贝马斯认为:“哲学也必须放弃其干预社会化过程的学说的传统形式,保持其是理论不变。最后,哲学再也不能根据价值的多寡把不同生活方式多样出现的总体性加以等级化;它只能把握一般生活世界的普遍结构。”(24)如果说马克思还因为哲学家只能解释世界而摒弃了当时流行的作为纯理论的哲学的话,那么哈贝马斯则相反,他要求哲学只作为理论存在。这个对哲学态度的明显反差部分地反映了西方哲学近代以来的嬗变。
然而,现代西方哲学既然已经放弃了对总体性或大全的追求,它又如何能“把握生活世界的普遍结构”?近代以来,哲学先是以自然科学为效仿的典范,继而试图与各门科学各司其职,最终在各门具体科学面前俯首称臣,乃至将自己限于对科学的结论进行一般解释与说明。而各门人文科学和艺术在现代的壮大,使得哲学再也无法垄断“生活世界整体关联的自我理解进程”。哲学的确对现代性危机进行了持续的批判,但这同样也不再是哲学的专利;相反,哲学的现代性批判不断挪用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艺术科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批判的武器和论据,这导致哲学家自己都认为哲学不再必要。今天,批判现代世界危机的主力早已不是哲学,而是上述各门科学。哲学日益退化为纯粹的学术工业和学院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学科。
与此同时,现代西方哲学与时代日益脱节,越来越具有“无时代性”的特征。19-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哲学以各种形式的现代性批判为其主要发展动力,但越来越走向学院化和技术化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个事实的典型标志恰恰是“语言学转向”。这个转向将哲学与时代逐渐隔开,意义和真理的问题不再是一个人生的问题,而只是语言问题;语言批判取代了时代批判。但西方哲学的这种现状恰恰也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问题:实质意义的缺失。人们可以承认语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形式意义,但除此之外却是意义的虚无主义——无意义;最多也是只有局部的、不可通约的、碎片化的意义,而不再有整体性的、贯穿人对世界和自己的所有理解和行为的意义。而这种意义的缺失,原因不止一端,但哲学放弃了对世界的整体统一性的追求,与这个世界一起分裂,却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由于哲学失去了其根本的内容,“理性萎缩成了形式合理性,从而内容的合理性变成了结果的有效性。而这种有效性则取决于人们试图据以解决问题的程序的合理性。”(25)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并未改变理论脱离现实的状况,反而加强了哲学与现实的脱离倾向,哲学日益成为纯粹的思维技术,或对思维条件、规则、程序的思维,哲学不再是形而上学,甚至不再是存在论。哲学的这种演变,以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方式,显示了现代和现代性的特征。
现代西方哲学虽然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但却是出于理论哲学的需要,它没有像古代哲学那样,关心人的灵魂和人的日常行为。它只对思维主体之“脑”有兴趣,对行为主体的“心”很少予以关注。它比较热衷人是如何想的,最多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研究和说明人的行为,却从不说明人的实践行动的德性条件。这其实是把人还原为没有自由意志和价值取向的纯粹自然有机体。虽然道德哲学不但没有在现代哲学中缺席,反而由于现代性本身产生的道德危机而成为哲学研究的热门,但现代道德哲学却同样是一种理论哲学(康德的道德哲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的兴趣主要在研究人的价值和行为习惯体系,分析阐明道德的基本概念、原理和命题,析解道德或伦理的构成要素。它本身并不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去做,尤其是如何使自己向善或变得更好。相反,它只是对分析善的概念有兴趣。正因为如此,“当今占统治地位的分析哲学或现象学哲学,都将无力觉察现实世界中道德思想和道德实践的无序状态,如同它们面对想象世界中科学的无序状态时无能为力一样。”(26)
此外,现代西方道德哲学从现代主体性出发,往往将他律和自律视为古代伦理学和现代伦理的根本特征区别:前者是他律的,即以天命或神旨作为道德的根据;而后者则以道德主体——人自身作为道德的立法者。根据现代性意识形态,这意味着人在道德上从神学和迷信中解放出来。然而,这种“解放”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从传统道德的外在权威中解放出来的代价是,新的自律的行为者自诩的道德话语丧失了任何权威内容。”(27)现代性无法为其道德信奉提出一个世俗的合理化论证。(28)现代世界的虚无主义和价值无政府主义实肇端于此。
西方伦理学从他律到自律的转换,一般而言,与现代性和现代世界的产生是同步的,或者说,它是它们的直接产物。导致这种转换的关键因素有二:宗教势力的衰退和以自然科学的模式为本来理解人与道德。这两个因素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经验自然科学纯粹根据各种生理和物理的机械作用来理解人,从而剥夺了人身上的神性和自由意志;这又导致宗教神学的进一步衰落。休谟已经清楚地看到,在一个经验的人的科学中,义务(obligation)概念是成问题的。科学解释实然,但它不能产生应然的规则,即人行为的规范性规则。(29)“规律”这个术语的意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不再具有绝对规范性的意思,而只是指始终发生的事或事物必然发生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内在于自然。(30)这样,道德就不再有超越的根据,其根据转到了道德主体——人的手中。
然而,真正的道德主体不可能是一个抽象的普遍概念,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从原则上讲,他们具有同样的作为道德的立法者的权利。这必然会产生如下的问题:“为什么所有其他人现在都应该听他的呢?”(31)而现代性的所有主要的道德理论,包括理性主义、情感主义和功利主义,证明都无法给道德提供一个普遍承认的根据,它们彼此在道德基础的问题上分歧深刻,更不能像古代伦理学那样,以使人向善为主要目的。
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大都将趋乐避苦理解为最基本的人性,将它作为道德的根据和基础,道德情感主义和功利主义都是这样。然而,正如麦金泰尔所分析指出的,苦乐作为人的感觉,总是主观相对的,不可能统一。“不同的快乐、不同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公度的:不存在任何尺度可用来衡量它们的质与量。”(32)“那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概念就是一个根本没有任何清楚内容的概念。”(33)因此,无论是道德情感主义还是功利主义,都无法给道德提供一个普遍接受的基础。相反,它们实际上剥夺了道德的基础,一方面把道德变成了一个“可供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使用的伪概念”,(34)另一方面使道德成为尼采后来一针见血指出的,只是主观权力意志的表现。
即使在沙夫茨伯里这样受到古代道德思想(斯多葛派)明显影响的新柏拉图主义者身上,道德根据的主观化倾向也表现得相当明显。他把道德判断的根源归结为“自然之爱”(natural affections),虽然他认为道德规范的基础在实在合乎理性的秩序。“爱”(affections)在他那里包括欲望、冲动、感情、情绪、基本性情,偶尔也包括激情。自然之爱指引心灵去做仁爱的行动,趋向生活的道德目标。人类必须积极地通过审慎地遵循他们自然之爱的方向去寻求善。是自然之爱把人们互相联系在一起。现在,道德的基础甚至都不在理性,而在于种种主观感性的因素。
哈奇森在大量吸收沙夫茨伯里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把自利作为人行为的根本原因,效益是善的准绳,从而把沙夫茨伯里的伦理学变成一种简单的后果论伦理学。物质利益,而不是像沙夫茨伯里认为的德性,才是道德完善的标准。虽然哈奇森认为有德之人应该为公众现实幸福创造社会条件,但是在他的成熟著作《道德哲学体系》中,他还是承认当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多数人会要自我利益。(35)在《蜜蜂的寓言》中,曼德维尔认为人的自爱根植于自我保存的本能,而自我保存的本能使人将自我利益置于他人利益之上。休谟不否认我们会考虑他人的利益,但他用同情心这种情感来解释我们对人类利益的兴趣。
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法国启蒙思想家在道德根基的问题上同样诉诸人的自然天性。伏尔泰与洛克一样,认为善恶观念不是“天赋的”,所以道德标准因地而异。虽然如此,但人在某些根本行为原则上还是一致的。在狄德罗看来,人性及其基本需要是普遍接受的善恶之别的根源。霍尔巴赫认为我们行动的种种动机就像物理规律那样起决定作用,它们实际上只是通过教育内在化了的生理原因。这样,道德行为就可以被最终理解为生理行为。道德的根据在于生理原因,而不是人的自由意志。
卢梭批评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是没有道德的看法:“我们尤其不可像霍布斯那样作出结论说:人天生是恶的,因为他没有任何善的观念;人是邪恶的,因为他不知美德为何物;人从不肯为同类服务,因为他不认为对同类负有义务。”(36)认为道德的根源在于我们的自然情感。驱使人们形成社会的,不是霍布斯认为的自我保全的本能,而是自然的怜悯心。“除了对弱者、罪人、或整个人类所怀有的怜悯心外,还有什么可以称为仁慈、宽大和人道呢?即所谓关怀、友谊,如果正确地去理解,也无非是固定于某一特定对象上的持久的怜悯心的产物。”(37)卢梭认为,如果人能行善,他们一定从一开始就是善的了,即自然人性就是善的。人天生之善包括人的各种激情,它们是人自爱(amour de soi)的中介。(38)道德在于倾听自己内心的自然之声,忠于自己本真的情感。
自律道德哲学一般是与康德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虽然康德受到卢梭很大影响,但他并不认为人性是善的;相反,他认为人性天生向恶,而不是向善。(39)正因为如此,人的自然情感,无论是否是道德的,都不能作为道德的基础,因为它们本身不具备道德基础所需要的无条件性和普遍性。(40)康德之所以反对把一切经验的东西——道德感、情感、功利、福乐作为道德的基础,就是因为它们不能满足这两个要求。他认为只有人的先验理性才能满足这两个要求,只有建立在理性绝对命令基础上的道德,才是无条件的和普遍的。在康德那里,善的观念不再是道德律的基础,而是反过来,道德律规定善与恶;善不再是道德的首要范畴,现在合理性才是道德的首要标志。先天合理性高于上帝意志、道德情感、人的完善和幸福。道德规范只能从理性的先天原理中演绎出来。
康德仍然认为追求人的完善是德性的本质,但人的完善本身需要用超经验的规范来衡量。服从理性规定的种种义务就是道德完善,因为理性的绝对命令指引我们趋向各种目的,这些目的是无条件善的。我们不是被迫、而是自愿服从理性的绝对命令,或者说,这些目的不是外来强加的,而是我们的理性意志自愿选择的,只是因为它们符合理性。道德立法的理性与道德主体的理性乃同一个理性。服从道德义务就是服从自己的理性,这就是所谓的自律道德哲学。
然而,自律的理性本身却不是没有问题的。道德自律的理性是实践理性,但康德自己也承认:“从一个存在者具有理性这一点,根本不能推论说,理性包含着这样一种能力,即无条件地、通过确认自己的准则为普遍立法这样的纯然表象来规定任性,而且理性自身就是实践的。”(41)即使理性是实践理性,它是否能发出一个无条件的命令还是有疑问的,因为理性本身必须在自然条件下存在,它自己不太可能是无条件的;即便是无条件的,也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得以实施的。(42)康德道德哲学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它的形式主义。它的经典表达就是:“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但只有在没有明确的内容规定的情况下道德规则才能普遍化,因为任何具体的道德行为都有不可重复的唯一性(特殊的道德行动者及其行动的条件和环境,等等);但没有具体内容道德律就无法被应用。(43)道德的难题就在于,它的原则和规范必须是普遍的,而这些原则和规范的实现总是特殊的。
此外,对于什么是“合理的”并不是没有歧义,同时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普遍认同。“合理的”在日常语言的用法中有两种意义:一是提供的理由普遍被认可;二是符合理性的推理程序和规则。前者实际上几无可能。彼得·温奇在《伦理学与行动》中曾指出,每个人在进入成年后都至少带有一套他很少会质疑的道德行为准则,那套行为准则会使他把某种特殊选择普遍化,但这种普遍化的方式与以别的道德行为准则生活的人的普遍化方式是不同的。(44)道德行为是否合理,涉及价值理性,而价值理性总是与人的历史存在相关,无法取得一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待奴隶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当然是合理的,但在现代人看来正相反。现代人觉得牺牲自然为自己谋利的做法“天经地义”,后代的看法也许恰好相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那么剩下的只能是第二种意义,即“合理”乃指合乎理性的思维规则和推理规则。正如查尔斯·泰勒指出的:“现代的理性概念是程序性的。要求我们做的不是沉思秩序,而是构建一个遵循理性思维准则的事物的图景。”(45)当康德要求道德从先天原理或观念中演绎出来时,已经指向了这个方向。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和交往行为理论也基本不脱这个思路。康德的这个思路在分析哲学家中也被奉为圭臬:“证明道德规则的权威性与客观性恰恰就是理性推理具有的那种权威性与客观性。因此他们的核心筹划过去是,现在也是,表明任何有理性的行为者都通过其理性从逻辑上信守道德的规则。”(46)理性实际上变成了工具理性或计算理性,它本身是价值无涉的,因而没有资格称为“实践理性”,因为实践(实践哲学意义上的)本身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
自律道德哲学的要旨在于理性自我立法,自愿遵守自我规定的道德法则。但是,作为自律道德哲学基石的理性,是唯理论的理性概念,它乃是近代世界的种种社会特征所致。这些社会特征把实践哲学的观念建立在一种特殊的对公共理性的理解上。“这种理解原则上要求每一个决定都建立在可以通过推理说明的根据上。”(47)这种理性的要求实际上是近代科层制理性的要求。这种理性其实是工具理性,它并不能证成道德,它的形式要求既不能赋予道德以任何实质内容,更不能证明任何道德规定的实质合理性。此外,只有理性才能保证事物的正当性,也是一个在现代越来越遭到挑战和质疑的现代性偏见。“理性是计算性的,它能够确定有关事实和数学关系的真理,但仅此而已。”(48)麦金泰尔的这话可能有点过头,但在有关价值和意义问题上,理性的作用的确是有限的,甚至并不是最关键的。
如果自律道德哲学并不能证明道德本身,那么它必然导致道德虚无主义也就不难想见了。事实上它不但不能证明道德本身,更不能促使人向善,不能像古代伦理学那样成为人们“好生活”的依据,而只能是现代学术工业的对象。德性伦理学的兴起反映了人们对这种现状的极为不满。这种不满当然不能认为仅仅是因为自律道德哲学的理论缺陷,而且更是因为现代世界道德的根本缺失。这种缺失在“上帝死了”的宣告中表露无遗。
从古希腊开始,哲学就是要通过理性的力量来让人知善恶,明是非,给予人的道德生活以指导。哲学在表明世界的合理性的同时,也表明道德生活的合理性。所以,西方有代表性的哲学家的哲学中都有一种伦理的动机。他们从来不认为哲学有两个不同的任务:认识世界、说明世界和指导生活。即便像康德那样,基于他的二元论哲学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分开来讨论,仍然坚持只有一个理性,实践理性是理论理性的基础,而不是相反。但现代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道德哲学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非哲学的内在部分。道德哲学完全可以与其他哲学研究分开来处理,而不再是哲学本身的基本组成部分。道德哲学不是人对自己意义的追求,而只是又一种以道德为研究对象的纯粹理论。
很显然,现代道德哲学的危机其实是哲学本身危机的一部分,也是由于现代性原则使然。现代性使得哲学最终放弃了它最初的追求。在《交往行为理论》导论一开始,哈贝马斯就指出:“哲学自其开始以来就致力于用在理性中发现的原理来解释世界整体,解释各种现象多样性的统一。”(49)但是,他又看到,哲学的这个传统现在遭到了质疑。哲学现在不再与世界、自然、历史、社会的整体性知识有关。这不仅是因为经验科学的发展,而且更是由于随着经验科学的进步,哲学对自身的反思所致。哲学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在一个科学惯例的框架里思考问题。哲学思想已经放弃了它的整体性追求,兴趣转移到科学理论的逻辑、语言理论和意义理论、行为理论,甚至美学,当然我们还可加上政治哲学等所谓的部门哲学或专门哲学。哲学变成了“Metaphilosophy”(后哲学)。哈贝马斯认为,这意味着哲学已经失去了它的自足性,哲学最初追求事物的最终根据的企图失败了。(50)
另一方面,一旦哲学不再是对事物的整体性的追问,而成为形式化的各种理性批判,哪怕也包括现代性批判,它本身几乎无法成为最终的结论,因为批判总是有其未必言明的形上前提或对存在的整体性的预设;而这些前提和预设本身不是推理得来的,而是先天假设的。此外,理性(reason)总是与合理性(reasonableness)相关;可是,事物的合理与否,在相当程度上不依赖理性推理的结果,而是非技术性的价值理性或实践理性的断定。人类总是先天秉持一些终极价值,是它们,而不是推理程序和过程构成了合理性的根据。这些根本性的认定,是超越理性的。当维特根斯坦说:“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就是这样的。”(51)他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作为整体的世界,即作为全体的存在是无法用理性说明或证明的;理性所能做的只是解释世界种种具体、特殊的表现方式,包括其中各种事物的运作与表现的方式。
如上所述,当代的哲学危机是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产生的。当现代性将世界分为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现象与本体,以及其他所有由此而来的根本二元分裂时,人类也就失去了万物一体的世界观,大全或总体性就成为形而上学的虚构而被彻底抛弃。另一方面,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分裂的世界观必然使得现代性哲学的方法论是用理论的态度,即认识理性的态度处理一切事物;它的基本问题模式必然是“是什么?”而不是“如何是?”它将一切问题都还原为此一模式的问题。但是,哲学从一开始,恰恰就不追求客观知识论意义上的“是什么”,而关心的是“为什么是”和“如何是”。因此,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哲学的危机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维特根斯坦说过:“一个哲学问题只有在正确的背景中才能得到解决。我们必须给这个问题一个新的背景,我们必须把它比做我们通常不作比较的情况。”(52)同样,要解决哲学的危机,我们必须将它放在一个新的背景,即批判现代性或现代性批判的背景中来思考和讨论。维特根斯坦自己正是这么做的。
与许多大哲学家一样,维特根斯坦始终将哲学本身作为他思考的焦点,他的主要哲学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是根据他对哲学性质的思考而提出和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理解就迥异于现代性对哲学的主流理解。在人们拼命要证明哲学与自然科学一样“科学”或表达了科学的精神或本质时,他在《逻辑哲学论》中明确指出:“哲学不是自然科学之一种。(‘哲学’一词应该表示在自然科学之上或之下的东西,但不是同它并列的东西。)”(4.111)“哲学不给予实在的图像,它既不能肯定也不能驳倒科学研究。”(53)这其实就有哲学的任务并不是追求自然科学所追求的客观知识,也不是描述自然科学的本质或内在逻辑结构,更不是对自然科学的拙劣模仿等意思。自然科学是理论,但“哲学不是理论,而是一种活动。”(4.112)这种活动是“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哲学的结果不是‘哲学命题’,而是澄清命题。”(4.112)
但是,在维特根斯坦这里,“澄清”不是把没有说清楚的命题用明白无歧义的语言说清楚,更不是赋予命题以严格的逻辑形式和结构,而是限定与划界:“它(哲学)必须划分可思考的东西,由此划分不可思考的东西。它必须通过可思考的东西从内部来限定不可思考的东西。”(4.114)他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道:“本书将为思想划一道界限,或者不如说,不是为思想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一道界限。”(54)也就是要明确哲学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
《逻辑哲学论》最后一个命题:“对于不能说的,人必须保持沉默。”(7)这很容易使中国人想起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话来。但两者只是形似,其实各有其不同的出发点。维特根斯坦上述命题,是出于他对西方哲学危机的诊断而提出的根本治疗方案。虽然自古以来,西方人就喜欢将哲学称为“科学”,只是到了近代,西方人才将自然科学而非哲学,作为科学的典范。这也导致了他们经常忽视哲学与科学的根本区别,即便看到两者的区别,也总是认为它们的区别只是内容上的,形式上则是完全一致的,即通过命题来表明各种知识主张。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是建立在此基本预设基础上,也因此成为一切理论思维的指南。
然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恰恰在于不知道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不但在内容上,而且也在形式上。哲学由逻辑和形而上学组成,形而上学的命题没有意义,因为它们事关超越(即在世界之外的事情)。因此,真正能说的(也就是有意义的)只有自然科学的命题;但它们恰恰与哲学无关。哲学的根本问题在于用自然科学的命题形式说命题形式不能说的事情,即无关意义的事,因为形而上学的命题是无关意义的(unsinnig)。(55)“哲学著作中发现的大部分命题和问题不是虚假的,而是无关意义的。因此我们根本不能回答这种问题,而只能确定它们是无关意义的。”(4.003)
但是,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无关意义而不能说的形而上学不是像在逻辑实证主义者那里那样是应该拒斥的对象。“意义”(sinn)一词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有特殊的含义,只有能被经验事物通过与其一致与否检验真假的命题,才能叫“有意义的”。形而上学的事情连说都不能说,也无关经验事物,自然是“无关意义的”,但不是“无意义的”(sinnlos)。不能表达(但能显示)的东西才是极为重要的东西,如逻辑、形而上学、音乐、宗教、伦理学、神秘的东西等,因为它们都属于生命的问题。“我们感到,即使所有可能的科学问题都被回答了,我们生命的问题仍然完全没有被触及。”(6.52)科学不能回答生命的意义问题。哲学虽然并不提供关于世界的知识,但却是自有其特殊的价值所在。维特根斯坦从未认为形而上学的问题是无意义(nonsense)的。他只是认为形而上学的问题无关世界的经验事实,超越了经验世界,而人们只能用命题有意义地说经验事实。如果人们用命题来说超越的东西,就会导致无意义(nonsense)。(56)
然而,维特根斯坦对形而上学和哲学始终有最高的尊敬,因为他和康德一样,认为形而上学植根于人的本性:“人有强烈的欲望要冲击语言的界限。例如想想人们对事物存在的惊讶。这种惊讶无法用一个问题的形式来表达,也没有答案。我们能说的任何事先天一定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冲击了语言的界限……不过这种倾向、这种冲击,还是有所指……我只能说:我不会小看这种人类倾向;我向它脱帽致敬……在我看来,事实是不重要的。但当人们说:‘世界存在’时,他们的意思与我心相近。”(57)这是因为,形而上学的倾向是人之为人之所在:“伦理学是出自想要谈论生命的终极意义、绝对的善、绝对的价值……它所说的东西对我们任何意义上的知识都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内容。但它记载了人类心灵中的一种倾向,我个人对此无比崇敬,我的一生绝不会嘲弄它。”(58)
人们往往以为,哲学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只有消极的“治疗”作用,即指出传统哲学问题乃出于对语言和逻辑的误用,该如何纠正,等等。殊不知哲学在他那里也有正面积极的作用,即给予对世界的一种整体性理解,或者说揭示世界的逻辑可能性:“哲学只是将一切显露出来,既不解释也不推论。因为一切都在那里明摆着,无须解释。”(59)这里说的“一切”(alles),当然不是指一切经验的事物,而是作为整体的存在可能性。哲学问题超验的整体性,使得“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一劳永逸地给出的;是不依赖于任何未来的经验的。”(60)哲学就是通过将世界的秩序重新安排,使得它一目了然。(61)因此,有人说他似乎有两种不同的哲学观。(62)只是那种积极意义上的哲学维特根斯坦说得相对少些而已。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的根本问题产生于误用科学命题形式来说一些没有意义(senseless)的话,即说些与经验事实无关的话,或根本就不是知识问题的话。治疗意义上的哲学,就是将哲学问题实际的无意义彰显出来以消除这样的问题。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问题根本就不是经验问题,哲学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误用语言引起的:“哲学是一场用我们语言的手段来反对理智着魔的斗争。”(63)具体而言,就是根据具体哲学问题描述语言的种种用法以表明哲学问题是出于语言的误用,因此,维特根斯坦一再强调,哲学不是解释而是描述,因为语言的用法——语法是世界秩序和我们思维与行动的先天前提,它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却又是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只能顺从但不能构造,所以只能通过描述才能使人们发现这“最显眼、最有力的东西”。(64)在此意义上,哲学不是理论,没有假设,没有解释;而是行动,彰显整体性秩序的行动。
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治疗意义上的哲学和给予总体的世界观()意义上的哲学是可以统一的:治疗是消除误用语言产生的哲学问题,这样就能以正确的方法从事哲学,以达成它的真正目的。
由于有些人往往不清楚维特根斯坦哲学与罗素和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而恰恰是在后者的影响下去理解维特根斯坦哲学,因而总以为维特根斯坦哲学前后期思想有明显的区别,是两种不同的哲学。其实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是因为没有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根本倾向有真正的理解所致。英国哲学家莫尔虽然认为《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在风格、进路,甚至(似乎是)学说上有影响深远和醒目的不同,但还是认为“在维特根斯坦的早期思想和他的后期思想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连续性”。(65)这种连续性首先就在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他因此把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称为是前期的“重演”(reprise),说《哲学研究》第89-133节提出了一种在所有意图与目的上与《逻辑哲学论》提出的完全同样的哲学概念。(66)
奥地利哲学家阿兰·雅尼克和英国哲学家斯蒂芬·图尔敏在他们合著的研究维特根斯坦的名著《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一书(此书的中译者把阿兰·雅尼克的国籍搞错了)中,用了很长的一章专门讨论“《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的连续性”,以及维特根斯坦与罗素和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67)维特根斯坦从一开始就像他所推崇的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一样,拒绝学派哲学家特别青睐的一种哲学活动,就是“抹掉(即混淆)”事实探究与概念探究之间的区别的哲学讨论。对他来说,这种讨论是“无意义的”。(68)《逻辑哲学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阐明这点。“要是对此书的最后五页(命题6.3以下),置之不理,书中其余部分展开的智识技术则在数学和哲学方面适合于多方面殊为不同的用途,而且还可以援用它们来支持那些与维特根斯坦本人南辕北辙的智识态度。”(69)可惜我们有些维特根斯坦研究者恰恰是这么做的,却还自信得了维氏的真传。维特根斯坦固然是在后期才明确提出“语言的用法”这个观念,“然而,引领他形成这一观念的理据就隐含在他的早期观点中”。(70)
当然,说维特根斯坦前后思想存在着连续性并不等于说它们完全一样,没有发展。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是围绕着语言用法的多样性展开的,而不是像《逻辑哲学论》的语言哲学那样,认为语言只有一种功能,即描述事物的功能。对于后期维特根斯坦来说,哲学的功能仍然是“治疗”,但此时意义与否的标准已非一端了;意义的界限是围绕着“用法”、“目的”、“实际后果”等来划的。但不管怎样,意义与否的基本原则没有变,这就是语言表达的东西是否对应于经验事实(关涉经验事实,而不仅仅表象事实)。在他看来,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是它模糊了事实研究与概念研究的区别。(71)哲学研究是概念研究,但形而上学的表达却看上去总是像一个经验命题,实际却是语法命题或概念命题,维特根斯坦因而又时常把形而上学命题称为“重言式”或“逻辑命题”。如果意义与否与是否表达或指涉经验事实有关,那么形而上学当然是无意义。
然而,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无意义”(nonsense)不等于不重要。恰恰相反,“无意义”者才是最重要的东西。维特根斯坦批评形而上学是因为传统形而上学用经验形式来表达不能这样表达的东西,而不是因为它处理的是不重要的事情:“‘Nonsense’是由于试图用语言表达应该体现在语法中的东西。”(72)形而上学处理的是非常基本的问题:“它要从根本上来看事物,不关心实际发生之事的具体情况。——它既不是产生于对自然发生之事的兴趣,也不需要去把握因果联系。它是出于这样的追求:即要理解一切经验事物的基础或本质。”(73)所以,他明确对人说:“不要认为我蔑视形而上学或嘲笑它。相反,我把过去伟大的形而上学著作归入人类心灵最高尚的产物之列。”(74)
维特根斯坦不是像许多人误以为的那样,是要消除形而上学或终结哲学;他的目的是要重新去理解哲学这发自人性深处的追求的性质,消除现代性思想对它的种种误解。对现代哲学观的批判并没有终结哲学本身,而只是清除会导致哲学归于消灭的误解:“我们摧毁的只是纸牌屋,我们清理这些纸牌屋的语言地基。”(75)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某种原已一直在我们眼前的东西。”(76)
阿兰·巴丢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是“反哲学”,所谓“反哲学”,按照他的解释,是“对哲学进行哲学式藐视”。(77)这显然是不对的。维特根斯坦不是“对哲学进行哲学式藐视”,而是对哲学进行了哲学式的重新审视。我们发现,他要反对的“理智着魔”,实际就是现代性的哲学对自身的理解。这种理解按照科学知识的模式和科学方法的要求去理解哲学,将哲学视为对普遍的知识形式的追求。它提供正确思维的标准和方法,进而提供各种观点和立场的内在理由。它告诉我们正当思维的步骤与程式,却不管善恶是非的根据。因此,它是中性的思维术,而无关价值。这样,哲学就失去了它一开始就有的实践本性,即它既是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又是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而成为纯粹的理论。而作为理论,它彻头彻尾是一种理性的事业;但理性本身却日益成为工具理性。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与现代性的主流哲学观背道而驰:哲学不是科学,哲学命题不是科学命题,它不提供任何新的知识,而只是要理解这个世界(包括人生)的根据和基础,它早已在我们眼前,只不过“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已。哲学的任务和使命是通过理解显示此一世界的本质。(78)本质不在事物的背后或内部,而就在我们眼前,是事物之为事物的条件。因此,它不需要解释,不需要分析和论证,只需要描述。维特根斯坦根本不是人们理解的“分析哲学家”,在他的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中,我们看不到论证、分析、推理、证明、证据等,只有描述。然而,这种描述不是照相式的描述,而是创造性显示的描述:“人其实只应该像作诗那样作哲学(Philosophie dürfte man eigentlich nur dichten)。”(79)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诗是用信息的语言写成的,但却不是用在给予信息的语言游戏中。(80)言下之意,哲学的表述可能看上去像是提供关于世界的信息,实际却是对世界本性的理解。哲学不是理论和学说,而是行动,首先是治疗我们理智魔怔的行动;所以,哲学是一个意志的事情,而不是理智的事情。(81)哲学最终是每个人必须为他自己做的事。另一方面,哲学不涉及知识,而只是世界的可能性:“人们可以用‘哲学’来命名一切新发现和新发明得以可能之前的东西。”(82)人们不免会想起黑格尔对“逻辑学”的定义:它是“上帝的展示,展示出永恒本质中的上帝在创造自然和一个有限的精神之前是怎样的”。(83)维特根斯坦与黑格尔对“哲学”的根本理解何其相似乃尔!
维特根斯坦并未谈论哲学危机,更没有要告别哲学,抛弃哲学;他只是认为西方哲学有病,哲学病还得用哲学来治,他要用一种新的哲学来治疗传统哲学的疾病。他没有像许多西方哲学家那样明确看到西方哲学危机与现代性的内在关系。然而,他对西方哲学的诊断和治疗,实际上却揭示了西方哲学危机与现代性思维的根本关系。他的哲学使我们看到,哲学的危机并不是因为哲学本身是一个没有价值而被人错认价值的事业;也不是因为现代世界已经不再需要哲学;而是因为哲学自身产生了病变;或者说,哲学自己不断背离自己的初衷而陷入深刻的危机。哲学必须重新思考自己在当代世界的正当性所在,必须超克现代性的哲学定位。在这方面,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提供了下列提示:
哲学并不提供关于事物的知识,而是追求理解世界之可能性及其逻辑(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前提,也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世界之道(用西方哲学的话来说,作为整体的存在或整体性)。哲学并不是说明世界的理论,而是理解世界的活动。因为哲学不是科学知识,哲学对世界的理解蕴含评价,而非价值中立,哲学应该体现世界的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首先体现在人生理解的合理性中,因为理解人生与理解世界是不可分的。“如果哲学探索就是发现存在的首要意义,人们就不能离开人的处境来研究,相反,必须深入这一处境。”(84)哲学不完全是理性的活动,而是知情意统一的活动。因此,当代学院形态的哲学是病态的哲学或不正常的哲学,因为它排斥了众多的语言游戏——生活形式。(85)西方哲学家中的有识之士也都对这种现代性的学院哲学持坚决的批判态度。针对西方学院派哲学家日益脱离现实世界的真实问题,梅洛-庞蒂指出:“为了将哲学的根基置于地球之上,需要的恰恰是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家。”(86)列维纳斯则认为传统西方哲学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我对他人的责任是一切社会结构的基础,他要通过将体现这种责任的伦理学确立为第一哲学来反对西方自我哲学的传统。而阿多则通过对古代哲学的阐释来提醒西方人,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实践”。(87)而这种哲学传统,已经被许多哲学家遗忘了。
中国传统哲学自然有它自身的种种问题,但是却对上述西方哲学的问题具有免疫力。首先,中国哲学持万物一体的世界观,始终在事物的整体性上看问题,始终要求哲学思想提供整体性的理解。其次,中国传统哲学从来是实践先于理论,主张知行合一、学行合一,从来没有发展为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理论、纯哲学。中国的哲学向来既是哲学,也是生活方式。第三,中国传统哲学没有主客体分类的毛病,自然也不会有由此分裂产生的种种问题。可是,由于国人近代以来按照西方现代哲学观来理解传统哲学和改造传统哲学,使得中国传统哲学也陷入了合法性危机。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其实是现代西方哲学危机的一个曲折变种。就此而言,解决哲学危机是今天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哲学对于人类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的话。在克服哲学危机的事业中,具有现代哲学病免疫力的中国哲学,其意义与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①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8页。
②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21页。
③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77页。
④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0-221页。
⑤参见玛格丽特·J.奥斯勒:《重构世界: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的自然、上帝和人类认识》,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
⑥参见Alexander Koyré,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57.
⑦Michael A.Gillespie,The Theological Origins of Modern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p.262.
⑧埃德温·阿瑟·伯特:《近代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82页。
⑨埃德温·阿瑟·伯特:《近代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第95页。
(11)参见Charles Taylor,Sources of the Self,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124.
(12)亚历山大·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邬波涛、张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13)参见Plato,Republic 546a.
(14)Michael A.Gillespie,The Theological Origins of Modernity,p.281.
(15)Charles Taylor,Sources of the Self,p.288.
(16)Jürgen Habermas,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85,S.33.
(17)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22页。
(18)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23页。
(19)I.Kant,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sche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Bd.29,Berlin:Walter de Gruyter & Co.,1980,S.9-12.
(20)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839-840。
(21)Jürgen Habermas,Nachmetphysisches Denke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88,S.26.
(22)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宣称,“哲学的破产清算问题”作为我们时代一个重要的文化问题显示我们时代困境的症候(W.Theodor 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trans.E.B.Ashoton,New York:The Continuum Press,1973)。
(23)Jürgen Habermas,Nachmetphysisches Denken,S.26.
(24)Jürgen Habermas,Nachmetphysisches Denken,S.26.
(25)Jürgen Habermas,Nachmetphysisches Denken,S.42.
(26)A.麦金泰尔:《追寻美德》,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3页。
(29)参见Bernard Williams,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148-149.
(30)Louis Dupré,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of Modern Culture,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p.112.
(33)A.麦金泰尔:《追寻美德》,第81-82页。
(35)参见弗兰西斯·哈奇森:《道德哲学体系》上册,江畅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6页。
(36)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东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98页。
(37)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01页。
(38)卢梭严格区分了自爱和自私之爱(amour proper),后者是不自然的过多占有和支配他人的欲望;而前者却是天生的,会自然发展为对他人的爱。
(39)康德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一篇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
(40)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批评道德感理论是“把一切都置于追求个人幸福的欲望之上”(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1页)。
(41)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页。
(42)“你应该”这个实践理性的基本命令式就表明了这一点,人要超越他实存的实然,或把应然变为实然。应然也许是无条件的,但实然总是有条件的。实践理性的实现一定是有条件的。
(43)参见Louis Dupré,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of Modern Culture,p.137.
(44)Louis Dupré,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of Modern Culture,p.138.
(45)Charles Taylor,Sources of the Self,p.168.
(47)Bernard Williams,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p.18.
(49)Jürgen Habermas,Theorie des kom munikativen Handelns,Bd.1,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88,S.15.
(50)张汝伦:《现代性与哲学的任务》,《学术月刊》2016年第7期。
(52)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论伦理学与哲学》,江怡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1页。
(53)L.Wittgenstein,Notebooks,1914-1916,G.E.M.Anscombe and G.H.von Wright,eds.,trans.G.E.Anscombe,Oxford:Basil Blackwell,1961,p.93.
(54)L.Wittgenstein,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Werkausgabe Band 1,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95,S.9.
(55)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尤其是《逻辑哲学论》的基本学说,只有最终与世界中的事实有对应关系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形而上学无关世界中的任何经验事实,所以它的命题是“无意义的”或“无关意义的”。
(56)参见K.T.Fann,Wittgenstein’s Concept of Philosophy,Berkley &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p.26.
(57)K.T.Fann,Wittgenstein’s Concept of Philosophy,p.28.
(58)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论伦理学与哲学》,第8页。
(61)维特根斯坦曾用一个生动的例子来比喻哲学显明世界整体性秩序:“一个哲学问题就像是探究社会的组成方式。它就像是一个社团在必须要有规则却没有写明规则的情况下开会:各个成员都有一种本能,使他们能在彼此相处时遵守某些规则,但一切也变得更难,因为没有明确宣布会议主题,也没有重新安排阐明各种规则。因此他们把他们的一个成员视为主席,但他并未坐在桌头,也没有任何办法将其识别,这使得事情更不好办。因此我们一起来安排秩序和阐明秩序。我们让主席坐在一个容易识别的地方,让秘书坐在他附近的一个特殊小桌旁,让其他普通成员坐在桌子两旁,如此这般……”(转引自Anthony Kenny,“Wittgenstein on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in Brian McGinness,ed.,Wittgenstein and His Tim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6)
(62)参见Anthony Kenny,“Wittgenstein on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p.2.
(65)A.W.Moore,The Evolution of Modern Metaphysics:Making Sense of Thing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222.
(66)A.W.Moore,The Evolution of Modern Metaphysics:Making Sense of Things,p.255.
(67)参见阿兰·雅尼克、斯蒂芬·图尔敏:《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第7章“维特根斯坦其人和他的后期思想”,殷亚迪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年,第236-279页。
(68)阿兰·雅尼克、斯蒂芬·图尔敏:《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第241页。
(69)阿兰·雅尼克、斯蒂芬·图尔敏:《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第243页。
(70)阿兰·雅尼克、斯蒂芬·图尔敏:《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第255页。
(71)L.Wittgenstein,Zettel,Oxford:Wiley-Blackwell,1981,§458.
(72)G.E.Moore,“Wittgenstein’s Lectures in 1930-33,” Mind,vol.64,no.253,1955,p.312.
(74)M.O’C.Drury,“A Symposium,” in K.T.Fann,Ludwig Wittgensten:The Man and His Philosophy,New York:Dell,1967,p.68.
(77)阿兰·巴丢:《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严和来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年,第24页。
(78)他很早就说:“我的工作已经从逻辑的基础扩展到世界的性质”(L.Wittgenstein,Notebooks,1914-1916,p.79)。
(79)L.Wittgenstein,Vermischte Bemerkungen,Werkausgabe Band 8,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94,S.483.
(80)L.Wittgenstein,Zettel,§160.
(81)参见Anthony Kenny,“Wittgenstein on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p.25.
(83)黑格尔:《逻辑学》上册,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31页。
(84)莫里斯·梅洛-庞蒂:《哲学赞词》,杨大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9页。
(85)维特根斯坦甚至认为西方语言都导致了一种坏哲学(参见Anthony Kenny,“Wittgenstein on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p.13)。
(86)莫里斯·梅洛-庞蒂:《哲学赞词》,第24页。
(87)皮埃尔·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张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47页。
免责 声明: 以上图文来自网络,贵在分享,不做商用,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内容为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公众号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