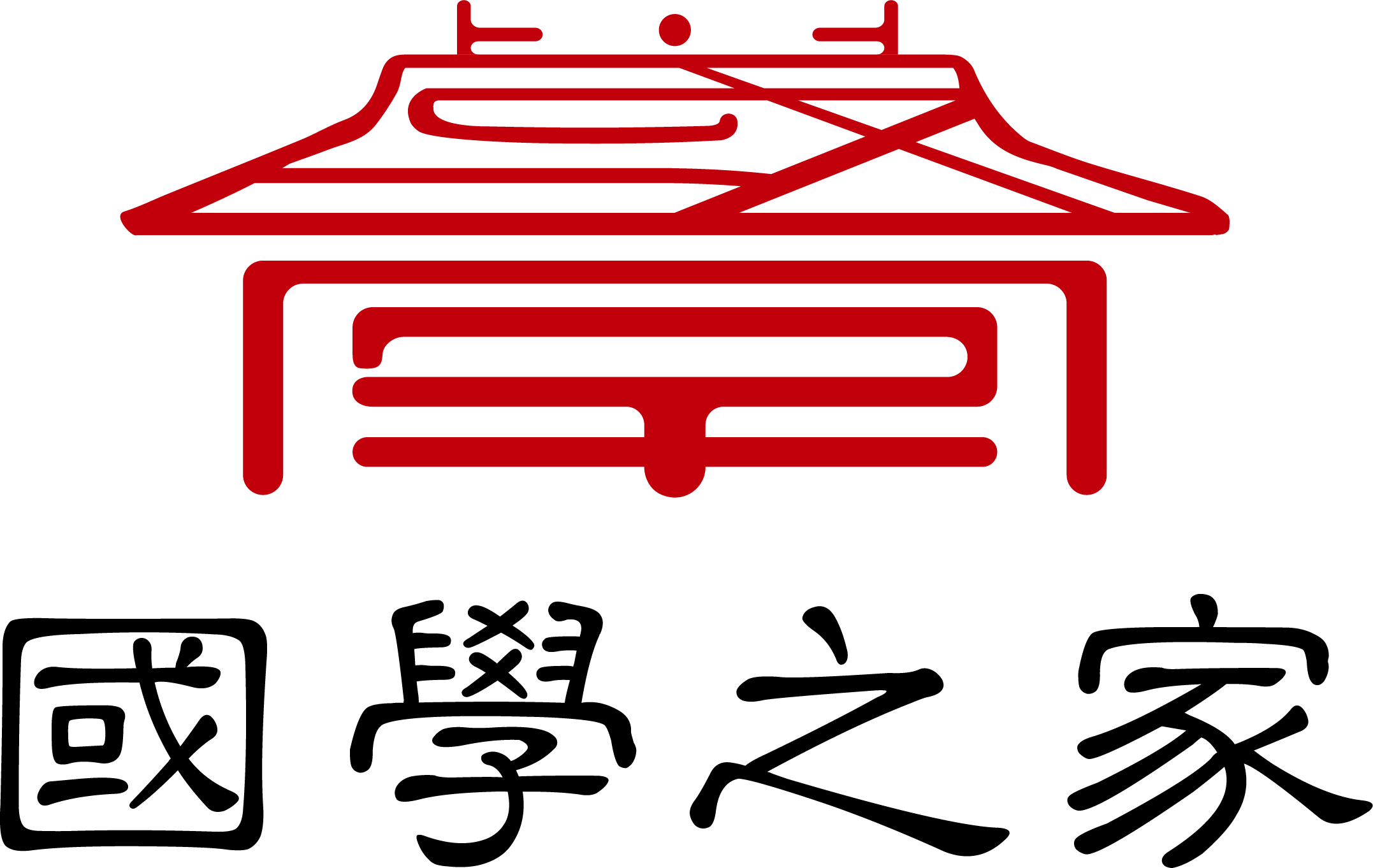解析两则神话的叙事系统,我们发现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叙事模式:同被受罚———同为人类的始祖神。
在中国,伏羲女娲生人的传说又与洪水故事发生了联系。据说人间百姓得罪了玉帝,故降大雨把百姓都淹死,只因天上一位神仙见伏羲女娲兄妹人品好,便赐一个竹篮或葫芦作为避水工具。洪水后,兄妹成婚,百日之后,女娲生下一个肉团,伏羲看后生气,便拿刀乱砍,砍下的肉陀一个个变成了人,恰好一百个,每人一个姓,这就是百家姓的由来。伏羲女娲生人神话之借助于葫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洪水背景下的伏羲女娲生人神话已是再造人类,而不是原始人了。肉团变人导出两种结果:其一是,说明百家姓之由来;其二,说明各民族及各民族分支之由来。怪胎及畸形儿,是对兄妹婚的谴责与惩罚,也可以看出原始先民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与观察,已对近亲婚配给后代造成的危害有了相当自觉的认识,已逐渐认识到严禁氏族内部通婚,而实行族外婚的必要,历史正是沿着人类的这种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轨迹,一步步演变前进的。
在两河流域的希伯来文化中,上帝是希伯来民族唯一信仰的神,他的地位独一无二,并且神圣不可侵犯,世间的一切都是由上帝创造并主宰的,所以人类必须绝对地服从和遵循其意志。因此,在长期的过程中,两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阶级差距,仅仅只是存在着单向的统治权,而人类所谓的自由、价值和生命意义都在于上帝的掌握。比如,夏娃由于蛇的诱惑与亚当一起犯了诫令而偷食了禁果,上帝知道后便严厉地惩罚了他们,在逐出伊甸园之后,罚亚当终生在地里劳作,罚夏娃在怀孕和分娩时遭受痛苦,这便是人类诞生之时犯下的“原罪”,从此每个人从一出生就走上了一条漫长的救赎之路,而获救的办法只有一个——信仰上帝,只有接受惩罚并虔诚地皈依上帝,才能找到终极基础和可靠保障。
(二)共同的视角:女性地位的缺失、男权地位的增强
女娲、伏羲共同生人,这不但昭示着中国古代由女性生人到男女共同生人观念的转变,同时也预示着中国社会由母系氏族时期向父系氏族时期的过渡。在各种史籍中,女娲仅以伏羲的妹妹和妻子的身份被记载,这显然是涂抹上了男权主义文化的色彩,更适合男权社会统治的需要,女娲不再是独立神,而成为了伏羲的配偶神。表明女性不仅在现实生活中,而且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下降了,男性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提升。随着男权制社会的发展,女性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不再处于主要地位,经济独立权丧失,地位进一步下降,逐渐由社会的主角滑向社会配角的位置。男权制进一步强化,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在所难免。
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终生屈从丈夫管辖,承受生儿育女的苦难与艰辛。而且在这里女性被认定为是人类堕落的渊薮,并认为男人被永远连累。女娲、夏娃神话就是这样为男权社会的合法化发放着通行证。这些神话也昭示人们,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当人类进入父权制时代后,父权是在不断地同女权残余思想进行殊死搏战中,彻底征服和剔除女权意识,才建构了惟我独尊的男权社会,男权文化和男权话语的。 这种叙事模式导引出的结果是:从此在东西方语境下形成了对男权地位推崇的文化母题。其次,两则神话都是以男性视角进行描述和判断的话语系统,为此,女人都被视为是男人的附属,女人的品格、意志和道德水准都较男人为低。这显然已是人类早期社会中男权取得统治地位时对女权消解的神话,男人已掌握了在氏族和社会上话语的权力,这种描述与判断中轰鸣着男性权力与地位不可凯觎的声腔。
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差异——伏羲女娲与亚当夏娃神话的文化价值比较
剖析这两则神话,进而放眼它们所生成时代的所有东西方神话,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在文化上的差异和区别。
首先,女娲神话是中国原始农耕文化意识的遗存。由于中国先民较早进入农业文明,所以,和伏羲女娲神话同时代或更早时代的中国神话,基本上都是农业文明时代的神话。而农业文明时代神话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希望构建一个天下太平,守土为安的生存环境。在社会生活中,具体表现为竭力稳固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关系。此外,农耕文明时代注重人丁兴旺。女娲既是古老的女性的“形象大使”,也是生殖文化的图腾范式。女娲与伏羲总是交合在一起,双尾缠绕是典型的生殖崇拜。
其次,农业文明的突出特征是定居生产。伏羲女娲神话从一个侧面向我们道出了农耕文明兴起时代的文化心态:守望家园,乐对人生,面视现实,这就是农耕文化经儒家化形成的华夏民族的人生信仰和道德规范。它导引着华夏先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守护着现世的家园。
亚当夏娃神话则是古代希伯来民族游牧文化时代的历史余音。上古希伯莱人和所有的游牧民族一样,驱赶着牛羊群,浪迹天涯,征服着每一块未知领域,追逐着理想之地——即水草丰茂的大草原,充满着冒险的激情。这种集体无意识深深镌刻在古希伯莱民族的精神碑石上。就当他们兴致勃发追寻理想之国时,天降大祸,他们又一次次被抛入苦难深渊,亡国之痛、灭族之灾,使全民族渴望着挣脱罪罚,远离苦难,重返天堂乐园。怡然丰裕的游牧生活被极尽艰辛的流亡生活所取代,追求、抗争、挫败、挣扎成为全民族的精神体验,而渴求幸福、安宁、和平的情感欲望最后在重返天国的契合点上凝结成新时代的民族文化精神。亚当夏娃神话实际上是古希伯莱人游牧流亡文化编码的变形改写,这种游牧文化是伴随着战乱与流亡生活联袂而行的。亚当夏娃神话以隐性话语叙述了古希伯莱民族社会转型期的文化演变结果。神话是民族的身份证,伏羲女娲与亚当夏娃神话以独特的话语结构,向我们解说了生活在亚洲东西两端的两个古老民族的文化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