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5月6日,顾颉刚在著名的论学书信《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石激起千层浪,宣告“古史辨”运动正式开启。此后的百余年间,毫不夸张地说,“层累说”一直是中国史学界的热点议题。然此文开篇第一句话“我二年以来,蓄意要辨论中国的古史”
(注: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页。) 中所蕴藏的“古史辨”运动的信息,却似乎没有引起充分注意。“二年以来”说明“古史辨”理论萌发于1921年前,而“蓄意”一词则告诉我们顾颉刚的辨伪思想酝酿已久且意旨明确。从顾颉刚及其学术同盟者留存的史料来看,“蓄意”所指的是他们计划编辑的《辨伪丛刊》 (注:对于《辨伪丛刊》的编辑,史学界已有一些讨论。如吴怀祺称《辨伪丛刊》是对古代辨伪文献作了一次整理(吴怀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马建强梳理了顾颉刚编撰《辨伪丛刊》的背景、有关撰述体例的思考〔马建强《个人际遇与学术生态的互动——顾颉刚学术生涯的突破》,《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60-64页〕;向燕南论述了顾颉刚《辨伪丛刊》中对郑樵思想的探究(向燕南《郑樵学术接受史之分析——从南宋到民初》,河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3-95页)。) 。

顾颉刚
一 《辨伪丛刊》的缘起与刊行
1909年,17岁的顾颉刚在中学老师张伯南的书架上第一次见到光绪十八年浙江书局本的姚际恒所著《古今伪书考》,即被姚际恒的辨伪言论深深吸引。1914年春,顾颉刚又从张伯南处借来《古今伪书考》,手抄一部,并于3月1日作了一篇长跋,称姚际恒为“山谷含章之士,不求令闻于世俗者” (注:顾颉刚《古今伪书考跋》,《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7,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页。) ,同时也批评了姚氏辨伪之不足,这似为顾颉刚日后编纂《辨伪丛刊》的远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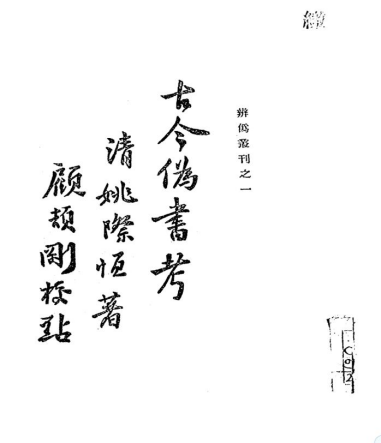
20世纪初年,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具有迫切的救亡心理,将中国所面临的困境归咎于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而如何整理与看待作为传统文化遗产和载体的中华典籍,学界聚讼未决。1919年,北大师生成立《新潮》和《国故》两社,前者以“学术原无所谓国别”,应“渐入世界潮流”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 (注:《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1919年第1卷第1号,第1页。) ;后者则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 (注:《国故月刊社成立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28日第298号,第4版。) 。胡适等人提出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是促成中国传统文化转向近代的重要方法与途径。这深刻影响了他的学生顾颉刚。1920年11月24日,胡适在给顾颉刚的信中写道,“我想先把《古今伪书考》抽出,点读一遍,做一个序,先行付印。……若你能任点读的事,就更妙了。不必急急,每天点两三页便够了。你若点读《伪书考》,再加上一点补缀,——如《尚书》及《周礼》等,——我定可担任寻出版者。此书版权即归你,我可以保他必销售” (注:胡适《嘱点读〈伪书考〉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6页。) 。可见,胡适从一开始就有点校《古今伪书考》的意思,并且有明确的出版计划。就这样,在胡适的鼓励下,顾颉刚标点《古今伪书考》,并发现了更多的伪书,如宋濂的《诸子辨》和胡应麟《四部正讹》。不止于此,顾颉刚较胡适更进一步,明确提出要编纂《辨伪书三种》:“我的意思,可以拿《诸子辨》,《四部正讹》,《古今伪书考》三种合印成一册,唤做《辨伪三种》。这三种合起来不过五六万字,可使人对于伪书得到更深的印象。” (注:顾颉刚《告拟作〈伪书考〉跋文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13页。) 胡适积极响应顾颉刚,称赞顾颉刚《辨伪三种》的想法“极好”,并指出“此书不妨慢慢地整理。或临时加入别的新发见的辨伪著作,亦未可知” (注:胡适《告拟作〈伪书考〉长序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15页。) 。在这两封信中,《辨伪丛刊》的计划已呼之欲出,略具雏形,只是还没有“丛刊”之名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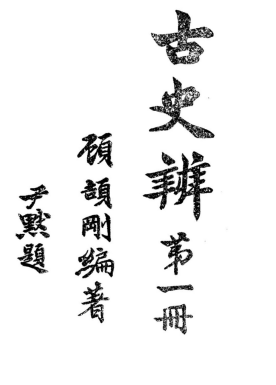
传统典籍浩繁,真伪难辨,前人虽多论述,然散见各处,难见其梗概。1921年1月25日,顾颉刚正式提出编辑《辨伪丛刊》的设想。这与另一位对催生《辨伪丛刊》具有关键作用的人物钱玄同有直接关系。这时的钱玄同正好也在密切关注前代史家的辨伪文字,同年1月8日,钱玄同专门购买了袁枚的《随园全集》,读后判定袁枚论《仪礼》、《中庸》为伪书,而“《经学迂谬》一篇,其言实有金汤之固”;三天后,他又购《崔东壁遗书》,认为“其辨斥传记传说之不足信,精当处极多,其辟妖异尤具只眼” (注: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69、370页。) 。由此可知,顾颉刚与钱玄同也是同道中人。顾颉刚在致胡适的信中指出:“钱玄同先生主张把辨伪文字一起集出,这固是很好,但一时恐不易辑录得周密。我的意见,不妨唤做《辨伪丛刊》;现在标点的三种唤做《丛刊》第一集。以后续得续刊,凡满十万字时,就成一个单行本。” (注:顾颉刚《致胡适:论伪史及辨伪丛刊书》,《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7,第241页。) 五年后,顾颉刚在回忆为何从《古今伪书考》走向《辨伪丛刊》时有更清楚的说明。顾颉刚因注解《古今伪书考》,对“古今来造伪和辨伪的人物事迹倒弄得很清楚了,知道在现代以前,学术界上已经断断续续地起了多少次攻击伪书的运动,只因从前人的信古的观念太强,不是置之不理,便是用了强力去压服它,因此若无其事而已。现在我们既知道辨伪的必要,正可接收了他们的遗产,就他们的脚步所终止的地方再走下去。因为这样,我便想把前人的辨伪的成绩算一个总账。我不愿意单单注释《伪书考》了,我发起编辑《辨伪丛刊》” (注:顾颉刚《自序》,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42页。) 。两相印证,可以确定,顾颉刚是发愿编辑《辨伪丛刊》的第一人。
1921年上半年,胡适、顾颉刚和钱玄同三人反复交流《辨伪丛刊》的内容、体例等问题。顾颉刚起初更在意伪书,在钱玄同的启发下,转而考虑“伪事”,并根据辨伪对象,一度有意将《辨伪丛刊》分为甲、乙两编,“辨‘伪事’的算做《辨伪丛刊》的‘甲编’,辨‘伪书’的算做‘乙编’” (注:顾颉刚《论〈辨伪丛刊〉分编分集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23页。) 。钱玄同主张“辨‘伪事’比辨‘伪书’尤为重要” (注:钱玄同《论近人辨伪见解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24页。) 。同年3月8日,顾颉刚将所拟《辨伪丛刊》总目送去胡适审阅,提出《辨伪丛刊》编辑条例三条:“1.十万字外、廿万字内,可一集。2.凡不是辨伪,或辨伪而不甚重要的,尽删削。3.每集略略断代。每编一集时,必将这一时代的书,就其重要的,略一检阅。” (注:顾颉刚《致胡适:二二》,《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1,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08-309页。) 这三条看似简单,实则明确了丛刊的篇幅,树立了精益求精和博采约取的原则。在这份总目中,顾颉刚将甲编辨伪事分为8集、乙编辨伪书分为17集,其中甲编包括“战国秦汉间人辨伪的话”、《论衡》、“六朝至唐代人辨伪事的话”、《史通》、“宋元明人辨伪事的话”、《黄氏日钞》、《考古质疑》、《易学象数论》、《考信录》、《史记志疑》、“清代人辨伪事的话”、杭世骏《质疑》、黄宗羲《破邪论》、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等,乙编囊括了汉至清共40余种专书和文集,涉及柳宗元、欧阳修、高似孙、宋濂、方孝孺、王世贞、顾炎武、万斯同、袁枚、崔适等,并辑录“唐以前人辨伪书的话”、“宋元人辨伪书的话”、“明人辨伪书的话”、“清代人辨伪书的话”等 (注:顾颉刚《致胡适:二二》,《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1,第309-311页。) 。后来正式出版的《辨伪丛刊》,所收书目基本未出此范围,显示出顾颉刚此时对古代辨伪资料已有总体认识,丛刊框架也已大体确立。胡适也为编辑《辨伪丛刊》积极谋划,建议“以伪书为纲,而以各家的辨伪议论为目” (注:顾颉刚《致胡适:三九》,《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1,第364页。) ,具体可安排为两部分:“(1)翻印古人辨伪的书,依年代为序,如他现辑的两集。(2)有些发生大问题的伪书——如《尚书》、《周礼》之类,每一部书可自为一集,汇集前人关于这书的辨论,依年代为序。例如《尚书辨伪》、《周礼辨伪》等。还可以提出更大的问题,如‘今古文的公案’、‘古史料的问题’等。” (注: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1页。) 这些讨论,有些最终未能实现,但对深化顾颉刚《辨伪丛刊》编辑思想有一定影响。不久之后,顾颉刚编辑《辨伪丛刊》的思路略有调整,不再区分“伪事”与“伪书”,理由是二者本难泾渭分明,无法截然分开,如“《考信录》是辨‘伪事’的,内中也带辨‘伪书’;《伪经考》是辨‘伪书’的,内中也带辨‘伪事’。所以我现在主张把两编打通了做,不设什么界限” (注:顾颉刚《答编录〈辨伪丛刊〉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32页。) 。《辨伪丛刊》实际编印时正是按照他的这个思路运作的。
1926年至1935年的十年间 (注:王煦华回忆《辨伪丛刊》的发行时间是“从1929年至1935年,共印了12种”(参见:王煦华《后记》,顾颉刚主编、王煦华整理《古籍考辨丛刊》第2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41页)。据笔者所见,《辨伪丛刊》第一种是1926年出版的《诸子辨》(参见:宋濂《诸子辨》,顾颉刚校点,《辨伪丛刊》之一,朴社1926年版,版权页)。另外,《古史辨》第1册也是1926年由朴社出版的。) ,《辨伪丛刊》陆续出版了12种图书,分别为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顾颉刚校点)、《论语辨》 (注:赵贞信辑点《论语辨》,上编、中编辑录崔述相关言论,下编汇辑柳宗元、袁枚、赵翼、康有为、崔适、梁启超、钱穆、钱玄同诸家学说。参见:赵贞信辑点《论语辨》,《辨伪丛刊》之一,朴社1935年版。) (赵贞信辑点)、郑樵的《诗辨妄》(顾颉刚辑点)、王柏的《诗疑》(顾颉刚校点)、《书序辨》(顾颉刚辑点)、胡应麟的《四部正讹》(顾颉刚校点)、《朱熹辨伪书语》(白寿彝编集)、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顾颉刚校点)、宋濂的《诸子辨》(顾颉刚标点)、高似孙的《子略》(顾颉刚校点),以上10种图书又总称为《辨伪丛刊》第1辑 (注:《辨伪丛刊》广告,廖平《古学考》书末附,张西堂校点,《辨伪丛刊》之一,景山书社1935年版。) ,另外还有廖平的《古学考》(张西堂校点)、《唐人辨伪集语》(张西堂辑点)2种图书。以上12种,除了《古学考》在景山书社出版外,其他均由朴社出版 (注:顾颉刚等人发起编辑《辨伪丛刊》之初,也考虑过在北京大学国学门或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书局1955年重版《辨伪丛刊》,书目略作调整,更名为《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参见:顾颉刚《论〈通考〉对于辨伪之功绩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37页;顾颉刚《序》,顾颉刚主编《古籍考辨丛刊》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王煦华《后记》,顾颉刚主编、王煦华整理《古籍考辨丛刊》第2辑,第641页。) 。这些著作既有从文集中抽出者,也有今人辑录者,或原书即为单行本,获取的渠道或借阅,或购买,印数多为1000册。《古今伪书考》、《诗疑》、《四部正讹》、《子略》等均曾再版,发行较好。为什么顾颉刚从1920年开始有意编纂辨伪文字,出版《辨伪丛刊》,但这些书多数在1930年以后才正式出版呢?对此,顾颉刚在1930年有过解释:“此十年中,时局的不安,生计的压迫,使得我频频南北奔驰,辨伪书的只出了《诸子辨》等三册,辨伪史的只出了《古史辨》一册。” (注:顾颉刚《序》,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顾颉刚校点,《辨伪丛刊》之一,朴社1933年版,第4页。) 此外,出版周期、等待序文等原因,也延迟了《辨伪丛刊》的出版时间。
顾颉刚动议并编辑《辨伪丛刊》时,有意将之打造为一个学术平台,以此凝聚学术力量。他在写给王伯祥的信中就透露出这个意图:“有史学的嗜好的,像你及绍虞等,总可以帮助我做去。将来我们有机会时,最好集合在一块。” (注:顾颉刚《致王伯祥: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77页。) 《辨伪丛刊》也基本实现了这一学术目的。在辨伪的旗帜下,胡适和钱玄同运筹帷幄,形成了以顾颉刚为主帅,白寿彝(1909-2000)、张西堂(1901-1960)、赵贞信(1902-1989)等为干将的辨伪学术共同体。在这个学术共同体的外围,还有为《四部正讹》写《校记》,并作《胡应麟传》的吴晗,有帮助校阅《子略》并作跋语的范文澜,有将《诸子辨》、《四部正讹》、《古今伪书考》合而观之,作《宋胡姚所论列古书对照表》 (注:此表附录于姚际恒著、顾颉刚校点的《古今伪书考》书末。) 的姚名达,以及众多关心《辨伪丛刊》的学者,比如白寿彝编《朱熹辨伪书语》的动机“是顾颉刚先生提起的。黄子通先生曾迭次催促它的完成,许地山先生给它题名子(字)” (注:白寿彝《序》,白寿彝编集《朱熹辨伪书语》,《辨伪丛刊》之一,朴社1933年版,第13页。) ,张西堂在辑点《唐人辨伪集语》材料的时候,得到了罗根泽先生的帮助 (注:张西堂《序》,张西堂辑点《唐人辨伪集语》,《辨伪丛刊》之一,朴社1935年版,第20页。) 。这些人同时也在古史辨运动和《古史辨》的编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辨伪丛刊》刊行后,在学术界引起的反响,甚至不逊色于《古史辨》。时人称赞:“近日《辨伪丛刊》照耀人目!凡中国向来今文学家未做完未说完之余沥,一跃而为新史界所啧啧鼓吹之新问题,前喁后于,当者披靡。” (注:侯堮《廖季平先生评传》,《中国新书月报》1932年第2卷第8号,第49页。) 1936年,《图书季刊》在“新书介绍”栏目也专门推介了《辨伪丛刊》,并在谈及这套丛书的学术价值时说:“我国古籍至繁,伪者亦众,苟不于著作人,著作时代及其所记者之然否一一辨明之,则伪品得以肆其欺罔,作史者必将错认虚言以为事实,而举世之人胥受其愚矣。” (注:《新书介绍:辨伪丛刊十一种》,《图书季刊》1936年第3卷第1、2期合刊,第79页。按:此篇名中称“十一种”有误,实为“十二种”。) 这话没有错,但只是针对一般意义上的史料学而言的,至于《辨伪丛刊》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真正价值,还在于它直接推动了顾颉刚“层累说”的形成。
二 《辨伪丛刊》与“层累说”的形成
“层累说”提出于1923年,时在《辨伪丛刊》正式编印面世之前。但从思想发生的角度来看,编辑《辨伪丛刊》的动议和运行在前,提出“层累说”及汇集古史讨论文章的《古史辨》则在后。人们多注意“层累说”和《古史辨》,却无意间忽略了《辨伪丛刊》。要知道《辨伪丛刊》是中国现代史学史第一次用科学的理念整理和总结古代史家“疑古的遗产”,是从传统史学出发,寻找“求真的微光” (注:顾颉刚《序》,宋濂《诸子辨》,顾颉刚标点,《辨伪丛刊》之一,朴社1926年版,第6、5页。) 。《辨伪丛刊》是“前人审查史料的总成绩” (注:《辨伪丛刊》广告语,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书末附,顾颉刚校点,《辨伪丛刊》之一,朴社1933年版。) 。顾颉刚始终主持斯事,辑录、研读前人辨伪文字,在古人的“总成绩”中发现了造伪的现象、规律,并在典型案例中破解“层累”的密码。可以说,围绕《辨伪丛刊》的校点、辑录及相关讨论,实际上为“层累说”的提出作了思想和资料的双重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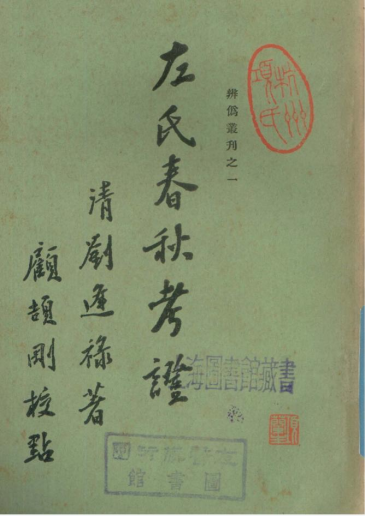
顾颉刚在阐述“层累说”时写道:
这段名言的思想意蕴可以用“拉长”和“放大”两个关键词概括。但顾颉刚这个认识不是1923年才形成的,而是他在编辑《辨伪丛刊》时已有发现。1921年6月,顾颉刚读到王柏《鲁斋集》卷4《续国语序》,发现此序在疑古思想发展史上价值颇高,故摘录200余字:“大抵翻空者易奇,核实者难工。异哉太史公之为书也!唐、虞之上,增加三帝:曰黄帝、曰颛顼、曰帝喾;论其世次,纪其风绩,惊骇学者,以吾夫子之未及知也。吁!学至于吾夫子而止;夫子之所不书,太史公何从而知之?”他并给予王柏“见解与崔述同……已经把难的方面做了”的肯定性评价 (注:顾颉刚《侍养录(二):王柏疑古》,《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卷1,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5-156页。) 。王柏探究孔子与司马迁二人对上古帝王的认识,指出: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晚于孔子,且先秦典籍经历秦火,为何司马迁却比孔子所知道的古帝王还久远呢?这与“层累说”中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何其相似!1922年,顾颉刚又在上海购得王柏的《诗疑》,读后再次被王柏的理性震动,“受了一个强烈的刺戟” (注:顾颉刚《序》,王柏《诗疑》,顾颉刚校点,《辨伪丛刊》之一,朴社1935年版,第1页。) 。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王柏对顾颉刚的“层累说”有先导意义。
1921年冬,顾颉刚“为了辑集郑樵的《诗辨妄》,连带辑录他在别种书里的《诗》论,因此在《通志·乐略》中见到他论《琴操》的一段话” (注: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5年第1卷第1期,第7页。) 。这段话原文如下:
郑樵由乐之演变而悟史之虚妄,从“得古人之影响又从而滋蔓之”,到数十言“演成万千言”的扩充、层积与叠加,这就是伪史的生成过程。“其理只在唇舌间”一语,道出了造伪者的荒诞。大致与此同时,顾颉刚将读书与观剧的心得写下这样一条札记:“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君主。《论语》上,问孝的很多,孔子从没有提起过舜。到了孟子时便成了一个孝子了,说他五十而慕,说瞽瞍焚廪、捐阶,说他不告而娶,更商量瞽瞍犯了罪他要怎么办,真成了惟一的子道模范人物了。想其缘故,或战国时《尧典》已流行了,大家因‘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一语,化出这许多话来。” (注:顾颉刚《景西杂记(三):舜故事与戏剧规格》,《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卷1,第256-257页。) 历史人物形象的变迁对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启发极大,让他认识到历史人物在流传的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存在一个重塑与丰富的过程。这不正是“层累说”中“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的原型吗?就连他所举的舜的形象构建事例也是一模一样的。
“层累说”另一个核心观点,是“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注: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60页。) 。这一思想也非突然萌生,我们可以在1921年1月顾颉刚与胡适讨论《辨伪丛刊》时所举的为孔子作史一例中发现端倪。他说:“我又想起,若是我将来能够做孔子的史,我决计拿时代来同他分析开来:凡是那一时代装点上去的,便唤做那一时代的孔子。例如战国的孔子便可根据了《易传》、《礼记》等去做;汉代的孔子便可根据了《公羊传》、《春秋繁露》、《史记》、《纬书》等去做。至于孔子的本身,拆开了各代的装点,看还有什么。如果没有什么,就不必同他本身做史。” (注:顾颉刚《致胡适:论伪史及辨伪丛刊书》,《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7,第241-242页。) 这里所说的“战国的孔子”、“汉代的孔子”,就是“战国时的东周史”、“东周时的夏商史”的同义置换!
顾颉刚编辑《辨伪丛刊》,是“要把中国的史重新整理一下,现在先把从前人的怀疑文字聚集,排比,做我们的先导” (注:顾颉刚《致王伯祥: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175-176页。) 。从效果来看,顾颉刚的确是在“先导”中逐渐丰富、发展辨伪思想,最终明确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重要古史学说。多年编辑《辨伪丛刊》的积淀,让顾颉刚胸中形成了一部中国古代辨伪史,他的辨伪智识得到了提升。
三 编辑《辨伪丛刊》与辨伪智识的提升
“智识”一词是顾颉刚编辑《辨伪丛刊》时的用语。结合他编印丛刊的收获和语境,顾颉刚所说的“智识”有胆识、知识和见识三层意思。下面根据顾氏“智识”之义,谈一谈《辨伪丛刊》对其领导疑古辨伪运动的意义。
首先,编辑《辨伪丛刊》增强了顾颉刚疑古的胆识。如前所述,顾颉刚的辨伪之路是从点校《古今伪书考》、编辑《辨伪丛刊》开始的:“我辨伪史的动机由于适之先生嘱我标点《伪书考》。故于《古史辨》第一册上编罗列了我们往来的信札,以志我走上研究伪史的路的起点。” (注:顾颉刚《序》,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第4-5页。) 顾颉刚20岁以前所受学术上的震荡之一,就是来自《古今伪书考》。他认为,姚际恒敢于提出“古今伪书”这个名目,“把以前人不敢疑的经书(《易传》,《孝经》,《尔雅》等)一起放在伪书里,使得初学者对着一大堆材料,茫无别择,最易陷于轻信的时候骤然受一个猛烈的打击,觉得故纸堆里有无数记载不是真话,又有无数问题未经解决,则这本书实在具有发聋振聩的功效。所以这本书的价值,不在它的本身的研究成绩,而在它所给予学术界的影响” (注:顾颉刚《序》,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第2-3页。) 。既然前人已经明白地指出古书与古史的造伪,为什么不可以继续从事辨伪事业呢!况且疑古者中多有名家,如王充、刘知幾、欧阳修、郑樵、朱熹、顾炎武等。因此,搜集的辨伪论著越多,顾颉刚疑古的勇气越大。整理、研究前人的辨伪言论,令他对这些疑古前辈心生敬佩,“把这些评论古书的文字汇集起来,是要一方面表示‘饮水思源’的敬意,一方面鼓起‘有进无退’的勇气;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能有这些鉴照是不容易的,一方面又要知道古人的成绩原来不过如此而已。这是我们印行这个《辨伪丛刊》的一点微诚!” (注:顾颉刚《序》,胡应麟《四部正讹》,顾颉刚校点,《辨伪丛刊》之一,朴社1929年版,第13页。) 顾颉刚宣称:“我们的成绩可以超过他们。” (注:顾颉刚《序》,宋濂《诸子辨》,第6页。) “圣人不是超人,乃是承受一代一代层积起来的智慧的人。只要我们肯把智慧层积起来,将来的圣人正多着咧!” (注:顾颉刚《序》,王柏《诗疑》,第25页。) 顾颉刚之所以有这样强烈的学术自信,一则他吸纳了前贤的优长,可谓知己知彼;二则顾颉刚受时势和新学的影响,思想得到解放,摆脱了传统的束缚。这份胆识,为他后来面对古史论辩中对手的问难树立了一道非常关键的精神屏障。
其次,编辑《辨伪丛刊》供给了顾颉刚丰富的辨伪知识。编辑《辨伪丛刊》是对古人辨伪活动的一次反思和整理,其间顾颉刚深刻领悟到古人辨伪的思想与视角,掌握了大量辨伪知识。胡应麟的《四部正讹》不仅考辨四部之伪,更可贵者在于自觉总结辨伪心得,认为“凡赝书之作,情状至繁” (注:胡应麟《四部正讹》,第1页。) 。胡应麟把伪书分为20种,包括:伪作于前代而世率知之者,伪作于近代而世反惑之者;掇古人之事而伪者,挟古人之文而伪者;传古人之名而伪者,蹈古书之名而伪者;惮于自名而伪者,耻于自名而伪者;等等。至于如何进行辨伪,胡应麟也根据上述伪书种类,略有提示:“凡核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核兹八者,而古今赝籍亡隐情矣。” (注:胡应麟《四部正讹》,第76-77页。) 胡应麟之论,从典籍流传上,紧扣史源及衍变;在内容上,把握叙事与文体;于时代演进中,思考宗旨与世风,总括了古人辨伪之智慧。顾颉刚读后,高度评价胡应麟的伪书分类,“在证据方面,心理方面,历史方面种种繁复的事实中寻出伪书的公例,确是一种很细密的创作”,只要掌握了这八种揭破伪书的方法,“即使像孙猴子一样,有七十二变的本领,也无所逃于如来的一掌了” (注:顾颉刚《序》,胡应麟《四部正讹》,第6-7、8页。) 。古人积累下来的这些辨伪知识与方法,大大提高了顾颉刚辨伪的能力。顾颉刚还通过研究崔述《考信录》,总结出“伪史例”,包括人物年寿(往往长寿)、数目(整数或乘数)、想象;至于造伪原因,“有的是要‘装架子’……有的是方士骗皇帝,求利禄,如《封禅书》所载。有的是为抢做皇帝而造的符命。有的是学者的随情抑扬。有的是学者的好奇妄造” (注:顾颉刚《论伪史例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29页。) 。凡此种种,皆表明顾颉刚已初步掌握了破除伪书与伪史的通例与方法。
再次,编辑《辨伪丛刊》提升了顾颉刚古史考辨的见识。顾颉刚较之王柏、崔述等古代辨伪大家的进步,主要有两点:一曰彻底的疑经,二曰无门户与党派。
先看疑经的彻底性。古代也偶有敢于疑经者,但毕竟是极少数。20世纪20年代,科学和理性成为时代潮流。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顾颉刚,已经脱离经学的羁绊,用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待六经。王柏囿于传统经史之学,以圣人所论为依据,“出于吾夫子之言,吾之所信也;其或出于诸子百家之书,非吾之所敢信也”,被顾颉刚斥为“因信孔子而辨伪史,不是因为疑伪史而辨伪史” (注:顾颉刚《侍养录(二):王柏疑古》,《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卷1,第156页。) ,这是传统学者背负的思想枷锁。《诗经》是儒家经典之一,也是顾颉刚《辨伪丛刊》所关注的重点,收录了《诗辨妄》和《诗疑》。在郑樵和王柏的基础上,顾颉刚主张:“孔子和《诗经》没有关系,删《诗》之说,本是汉代人的话,始见于《史记》,不足征信。但他们把后来人造成的孔子观念硬推到孔子身上,实也不对。孔子时的道德观念,施于家庭的是孝弟,施于社会的是忠信,施于自己的是俭节。至于贞淫的事,当时并未成为问题,《论语》上绝未说及。……万氏等认定圣人之书必有贞而无邪,有醇而无疵,认定《五经》是修身书,硬要把周代社会真实的记载抹去,实在太无历史的见解了!” (注:顾颉刚《景西杂记(三):〈诗经〉中之情诗与孔子删定说之矛盾;〈诗序〉之附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卷1,第251页。) 顾颉刚反复强调区别于崔述的“儒者的辨古史”,要做“史家的辨古史” (注: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59页。) ,意即在此。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崔述推翻了‘传纪’,回到几部他认为可信的‘经’。我们决定连‘经’都应该‘考而后信’” (注: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续)》,《现代评论》1926年第4卷第92期,第16页。) 。显然,《辨伪丛刊》的编撰,冲破了经学之桎梏,促使传统考辨之学迈入近代的学术谱系;而顾颉刚之论,则将经典与圣人分开,从科学辨伪的角度完成了古今学术的接续。
再谈无门户与党派。顾颉刚称:“我们辨伪,比从前人有一个好处。从前人必要拿自己放在一个家派里才敢说话,我们则可以把自己的意思尽量发出,别人的长处择善而从,不受家派的节制。譬如《伪经考》、《史记探源》等书,党争是目的,辨伪是手段;我们则只有辨伪一个目的,并没有假借利用之心,所以成绩一定比他们好。” (注:顾颉刚《致钱玄同:三》,《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1,第530页。) 目睹前人因门户之见或政治偏见而导致辨伪的受限,顾颉刚引以为戒,遂有此番自觉,将政治与学术分离,经学不再被视为“常道”而万世不朽,而是成为厘清古史面相及其衍变轨迹的史料。此时的顾颉刚崇尚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宗旨,在辨伪上的态度也是如此。
编辑《辨伪丛刊》,还让顾颉刚找到了辨伪的方向。他说:“《辨伪丛刊》只是集前人的文字,将来我自己想做三种书:(1)《伪史源》,(2)《伪史例》,(3)《伪史对鞫》。”他接着解释做这三种书的意图:“所谓源者,其始不过一人倡之,要在这时辨来,自是很易;不幸十人和之,辗转应用,不知其所自始,甚至愈放愈胖,说来更像,遂至信为真史。现在要考那一个人是第一个说的,那许多人是学舌的,看他渐渐的递变之迹。所谓例者,做伪史的总有一色的心理,记一事必写到怎样的程度,遂至言过其实,不可遮掩。现在要拿这般的心理归纳起来,教人晓得伪史总是欢喜向那方面走的,也可处处防范。所谓对鞫者,大家说假话,不能无抵牾,我们要把他们抵牾的话集录下来,比较看着,教他们不能作遁辞。……我们这样做,必可使中国历史界起一大革命。” (注:顾颉刚《致王伯祥: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176页。) 尽管顾颉刚并未能完成这三种书,但此间所形成的思想和相关活动确实在随后的中国史学界掀起了一场革命。
四 结语
蔡元培于1936年5月15日为新版《崔东壁遗书》题词时写道:“顾君颉刚作《古史辨》,印《辨伪丛刊》,对于甄别古书之工作,几认为终身事业。” (注:蔡元培《亚东图书馆新印顾颉刚标点本〈崔东壁遗书〉题词》,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无页码。) 蔡氏将《古史辨》与《辨伪丛刊》联系在一起,评估顾颉刚的辨伪事业,思考《古史辨》与《辨伪丛刊》之间的学术关联。在时间上,《辨伪丛刊》的编印与《古史辨》前五册出版同步。前者为辑录古人辨伪文字,后者是汇集时人论辨文章,具有相互声援和古今融通的学术效果。《辨伪丛刊》的面世,向反对疑古派的一方阵营充分展示了古代史家辨伪的业绩,吸引了更多学者关注和参与古史辨,有力地推动了“古史辨”运动的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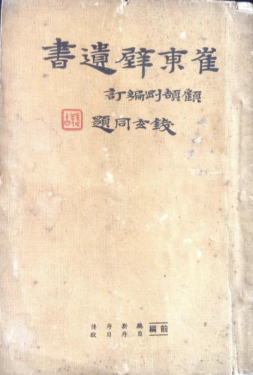
编辑《辨伪丛刊》是新文化运动后顾颉刚对传统典籍的一次清理,目的在于建立科学化的历史谱系。换言之,顾颉刚辨伪的目的不是停留在推翻伪书和伪史,而是重建信史。然而,古史资料有限。因此,他对伪书并非一概弃而不用;相反,他提出要思考伪书的成书年代和思想背景,并将其作为考辨古史及还原历史风貌的重要材料。他指出:“我们所以不能丢去伪书的理由:(一)用之已久,影响甚大;(二)用史的眼光看,作伪状况也是史;(三)可以考一个人或一种学说迁变的样子,可以知大家对于他的观念怎样。” (注:顾颉刚《景西杂记(三)·伪书不能废》,《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卷1,第259页。) 30年后,顾颉刚仍坚持认为:“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例如《易传》,放在孔子时代自然错误,我们自然称它为伪材料,但放在汉初就可见出那时人对于《周易》的见解及其对于古史的观念了。……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我们破坏它,并不是要把它销毁,只是把它的时代移后,使它脱离了所托的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应而已。……实际上真和伪往往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不能这般地截然分开处理。” (注:顾颉刚《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序》,《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7,第27-28页。) 无论《辨伪丛刊》,抑或“古史辨”运动,皆是近代以来新史学需求下的一种探索,将后世附会于经史的旨意“归还”于历史,并辨别真实与故事。这是顾颉刚在编辑《辨伪丛刊》的过程中强调的,也是贯穿于“古史辨”运动的一个核心理念。难能可贵的是,顾颉刚看到了传统史家辨伪质疑的魄力与束缚于枷锁的无奈。顾颉刚倡导“疑古”,以审慎的态度编纂《辨伪丛刊》,既继承了传统史家的辨伪成就,又打破了传统的局限,在辨伪的方法及宗旨上迈向了科学的道路,成为促成 “古史辨”运动的最重要一步。
本文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第35-41页。获取pdf文档请点击“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