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伎艺,传食于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
在叶氏眼中,富户的作用几乎无所不在,既为天子养小民,又为天下养天子,可谓全天下的衣食父母。既然如此,富人为谋利取财,怎么做也不算过分。
与叶适同为南宋功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陈亮(1143—1194),尽管没有太多直接论述,然其关心富户利益,强调富户对于国家财赋及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富民应该受到保护的思想倾向却非常显著。另一著名思想家真德秀(1178—1235)的观点与叶适基本一致,其要点是富户乃贫民依恃之一,若富民不能自存,贫民生计将更加窘迫。
富户在社会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自然应该加以保护,保护富人的财富和合法权益,同时提高富人济贫救荒的积极性,而不是相反。这样,富户才能有热情、有条件、有能力济贫救荒。而官府抑兼并、禁私债等有针对性地压制富人、扶持贫弱的做法自然是荒谬无理之举了。叶氏在《民事下》接着指出:
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此可随时施之于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为治也……夫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为治者也。
他认为,应罢儒者复井田之学,损俗吏抑制富人之意,因时施智,观世立法。“不然,古井田终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复立,虚谈相眩,上下乖忤,俗吏以卑为实,儒者以高为名,天下何从而治哉。”叶氏之说颇具深意,重点在于正视现实,顺应时代变迁。他抓住“井田之制不可复”这个所有问题的关键所在,明确倡导观世立法、因时建制之政治主张,并在此原则下理解、调控贫富关系,其积极意义显然不可忽视。
对于真德秀所云当时存在的地方官有意剥夺富家大户之类的行为,不少人表示了担忧或反对。较有代表性的是蔡戡,他提出:“夫单产贫民固在矜恤,富家大室犹欲全安之者,盖君民相通,富藏于民故也……富家大室一丽于法,喜动颜色,如得奇货。词所连染,追逮系累;搜摘隐微,强伏其罪;轻者出金以赎,动辄千缗;重者诋以深文,籍其资产;或幸免于戾,不复兴词,或已破其家,无力控诉。为守令者方且自谓得计。比年以来,所在富家大室衰替无几,职此之由。”我们从中了解蔡氏保富看法的同时,亦可窥见当时地方官府剥夺富家大室的状况。检阅文献不难发现,各地皆不同程度地存在官府强令免追私债、强发富人米谷,甚或借事抄没家产等侵夺富户的现象。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王安石被视为官府直接剥夺富户的代表,受到不少人的指责。苏辙即于指责王安石之时,阐发了自己的贫富观:“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然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忧,亦非所当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及其得志,专以此为事,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有意思的是,苏辙是在论诗时对王安石提出批评的,他认为王安石推行青苗法与此前王安石的一首诗大有干系,因此是一场诗病。“源其祸出于此诗,盖昔之诗病未有若此酷者也。”后世反对官方过多干预贫富之间关系的呼声甚高,当与王安石的实践和叶适、真德秀等人的倡导大有干系。
元明清三代,中国社会的变化较之宋代更为广泛深刻,不少思想家继承了前述宋代对贫富关系的认识及具有保富救荒倾向的思想,且加以发挥、发展,对当朝荒政及整个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丘濬(1421—1495)所著《大学衍义补》对贫富关系、富户作用等有明确的阐述,其保护富户的思想倾向相当明显。如该书卷13称:
诚以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小人无知,或以之为怨府。先王以保息六养万民,而于其五者皆不以安言,独言安富者,其意盖可见也。是则富者非独小民赖之,而国家亦将有赖焉。彼偏隘者往往以抑富为能,岂知《周官》之深意哉。
同书又云:“近世乃有恶富人冒利者,一切禁革民间私债,其意本欲抑富强,不知贫民无所假贷,坐致死亡多矣。”丘氏所见,与前引叶适之说如出一辙。不同的是他从“安”字切入,以阐发先王之意为意。
明代名臣徐阶(1503—1583)立足于业佃关系论述保护富人、富户救贫问题。其《复吕沃洲》书云:“大家有田而不能耕,必以属佃户;佃户欲耕而不足食,必以仰大家。其情与势,不啻主仆之相资,父兄子弟之相养。故大家于佃户,虽或不能无虐而不敢甚虐者,惧莫为之耕也;佃户于大家,虽不能无负而不敢尽负者,惧莫为之贷也。正德以前,民生裕而乡无恶俗,国赋登而狱鲜系囚,由此道也。迩年以来,有司数下讨债之禁,又重之摊放之刑,于是佃户嚣然动其不义不信之心,而大家惴惴焉,惧入于有司之罟。昔之所谓相资相养者,始变为相猜相仇,不惟债不可取偿,而租亦多负矣。债不可取偿,其始若止于病大家,而不知佃户无所仰给,则不免于坐毙。租之多负,有司者莫不欣然自诧其茹刚之政,以为前无古人,而不知租无所入,则税无所出,积之而久,逋赋日滋,刑辟日众,则己亦且受其累。”徐氏继承了朱熹的业与佃(富与贫)之间有相须相恤关系的思想,甚或进一步表述为“主仆相资”“父兄子弟相养”。更值得重视的是,作为当时权倾一时的人物,徐氏认为明正德以后业佃关系由“相资相养”一变而为“相猜相仇”,主要原因之一是地方有司或者说官府直接干预业佃关系,推行了带有抑富右贫倾向的政策。他之所以力主大家富户“各恤其佃户”,目的就是要取消或阻止官府“数下讨债之禁,又重之摊放之刑”之类的干预。其说当时就被批评者“直指为士夫自利之私谈,又或以为庇富人而代之游说也”。如果考虑到徐氏不仅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大官僚,同时还是一个占地面积广大的土地所有者这一背景,则时人的批评颇发人深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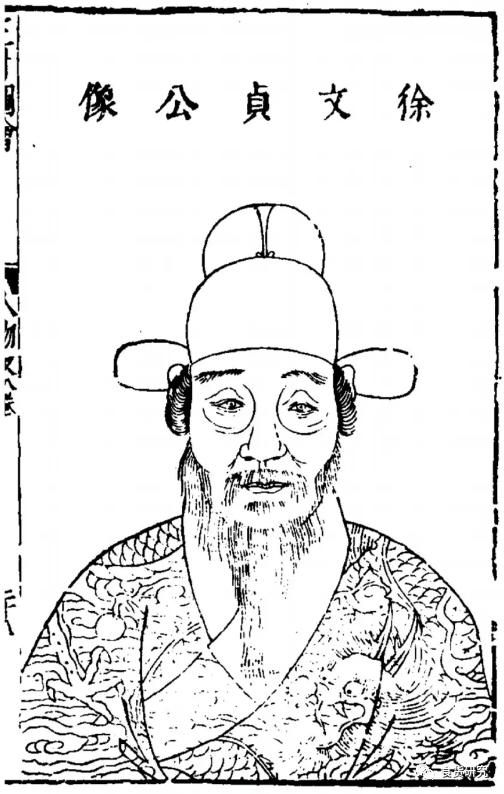
里有千金之家,嫁女娶妇,死丧生庆,疾病医祷,燕饮赍馈,鱼肉果蔬椒桂之物,与之为市者众矣。缗钱锱银,市贩贷之;石麦斛米,佃农贷之;匹布尺帛,邻里党戚贷之;所赖之者众矣。此借一室之富,可为百室养者也。
千金之富,可惠戚友;五倍之富,可惠邻里;十倍之富,可惠乡党;百倍之富,可惠国邑;天子之富,可惠天下。
无论是富户的数量,还是富户的财产,皆多多益善。
王夫之(1619—1692)没有局限在井田难行退而求限田这一解决贫富不均问题的传统思路中,而是明确主张土地私有,反对土地兼并。因此,他高度肯定富民的作用,“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尤其注重富户在救助饥荒时的作用。“卒有旱涝,长吏请蠲赈,卒不得报,稍需岁月,道殣相望。而怀百钱,挟空券,要豪右之门,则晨户叩而夕炊举,故大贾富民者,民之司命也。”富户能够起到的作用,恰恰是官府所不易起到的作用。
李雯继承了宋人叶适的保护富民思想,认为富民上供天子,下养百姓,乃社会经济生活的中坚力量。“贫者不立,富者以资易其田,捐半租与贫民而代其赋”,故“富民者,贫民之母也”。“今贫民无资寄种,不可得而役;游民转徙浮生,不可得而役。陛下之所役者,独富民耳。”所以,朝廷应该尊重、保护富民,打击地方官吏盘剥富民的行为。“然则陛下之富民,天子且护恤之矣,官长安得而辱顿之哉?官长不得辱顿之矣,群下安得而溪刻之哉?”不过,李雯所保、所恤之富是有区别的,权贵豪强靠特权致富与一般富户靠勤力致富是不同的,前者应不在保、恤之列。
清代能臣如那彦成、方观承以及救荒思想家杨景仁等人,都把主佃说成“相依为命”的关系,恤贫和安富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贫民未尽绥辑,富民岂能独安?是救饥济贫不特为善之首务,亦未必非保家之良策也。”方观承有《劝业民恤佃示》《劝当商减利示》,杨景仁作《安富以救贫说》《救灾有福说》等,较系统地阐述了保护富户赈济贫民、地主赈济佃户的思想。
窃谓善人者,国家之正气,富民者,国家之元气也,非富无以行善……凡以不积谷不足救饥,故能藏谷者,为之弛役行赏,使民晓然知富之见重于上,而各保其富焉。恭读《周官义疏》御案曰:安富尤保息之大者,盖富者不安,则民不务积聚而失其养者众矣,上岂能遍给哉。……地方有公事,亦惟富室是问,官吏或从而侵侮之,日削月朘,不久成贫……富者不安而日流于凋敝,设令饥荒荐臻,库帑不敢擅动,常平、社仓米谷之发又复不敷,将何取资以活环而待哺之穷黎耶!惟培养富户于平时,而后临事得借其力……夫周贫者之急不可以扰富,留富者之余斯可以救贫。
任恤之行于乡,大抵借富者之资,而其事足以辅当途之荒政。天非私富一人,托以众贫者之命,酌盈以剂虚,天道自然之理,即富者当然之分也……富莫保其富,则救贫之资无所出,贫者之不幸也;贫莫救其贫,则保富之计无所施,亦富者之深忧也。
对如何劝谕富户、业主出粮赈荒,杨氏也进行了认真的总结,的确是将其作为救济饥荒的重要途径来探讨的。
鲁仕骥、惠士奇、彭世昌等皆肯定富民为贫民之母,乃济贫救荒之主要力量。彭世昌《荒政全策》云:“良以富者,贫之母也。一邑有富民,则一邑缓急可恃;一乡有富民,则一乡缓急可恃。若富民凋敝,贫民何依?设遇灾歉,更何所恃乎?是在贤有司于无事时加意护持,而后有事时得赖其力,如平粜、助赈、施粥诸举是也。”惠士奇则云:“富民,贫之母也,病其母而不能活其子,亦何利之有焉。”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诸帝皆重视民间相互救助,极力倡导贫富相维、闾里相济、田主赈济佃户诸济贫救荒对策,视此为社会稳定的法宝之一。雍正曾谕富户云:“各富户等平时当体恤贫民为念,凡邻里佃户中之穷乏者,遇年谷歉收,或值青黄不接,皆宜平情通融,切勿坐视其困苦而不为之援手,如此则富户济贫民之急,贫民感富户之情。居常能缓急相周,有事可守望相助;忮求之念既忘,亲睦之心必笃;岂非富户保家之善道乎!”“富户之自保其家,尤富户之宣力于国也。”乾隆则云:“贫固资富之食,富亦资贫之力,不计其食而但资其力,穷民复何所图?”嘉庆更有“贫富有丰啬相济之情,业佃尤有缓急相通之谊”之说。彼此相安共处,可以消患于未然。这既是富户保家之道,亦为社会稳定所必需。不过,对富户之仁行义举,却只能劝行,不能强迫,更不可以官法相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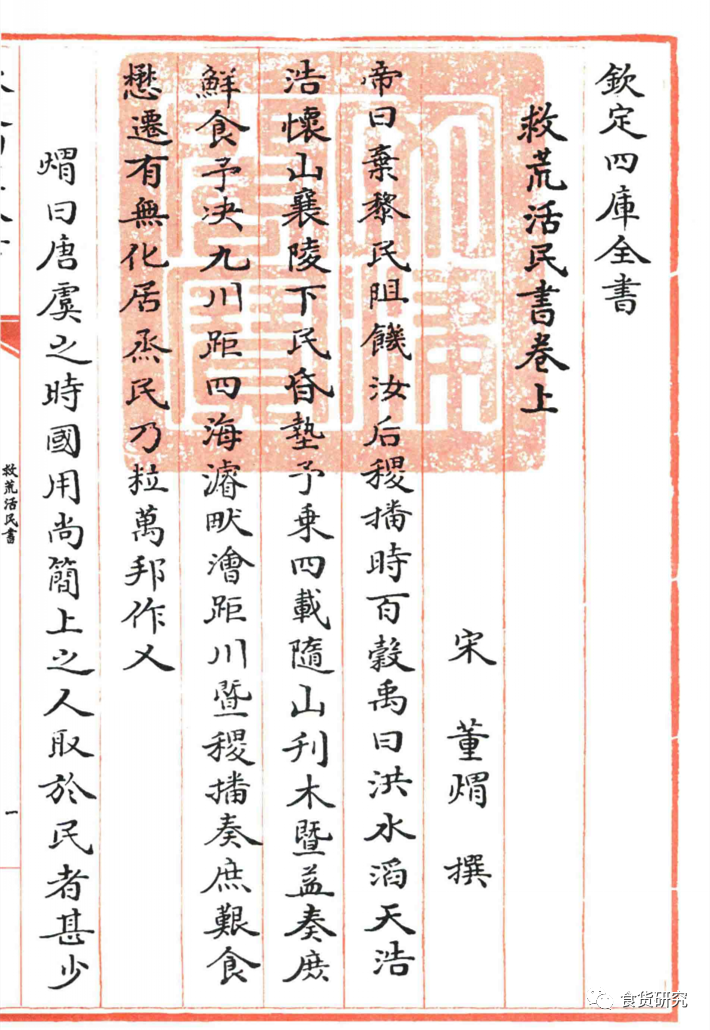
尝以为天下之患,不在细民之穷,而在富民之穷。善治天下者务使富民宽然有余,斯穷民得所养而不致失所。假如一郡能多得富而好德之人,则一郡之穷而无告者,皆可望其周恤而安全之,使之相维相系,不致流为盗贼而驯至于寇乱。一乡能多得富而好德之人,则一乡之穷而无告者,皆可望其周恤而安全之,使之相维相系,不致流为盗贼而驯至于寇乱。故富民者,穷民之命,国家之府,朝野上下元气之所关,匪细故也。顾无如世之为富不仁者比比也,不亦重可惑哉!
很显然,他对“足谷翁”为富不仁及“以身殉财”的批评是善意的,甚或可以说他认为一般百姓贫穷没什么,富民之穷才是社会的根本问题。对富民乃“穷民之命”“国家之府”“朝野上下元气之所关”的高度肯定,才是其思考的主旨所在。
其二,保富救荒思想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上述各家,无论持何种观点,无不引经据典,而且所据高度一致,即《周礼》关于安富恤贫的论述。《周礼》“以保息六养万民”的简要论述,为后世论者阐发各自思想留下了充分的余地,以至出现了悬殊的看法。然而,与此前相比,宋以后论者大多摆脱了仅止于引经据典的“空”发议论的局限,立论基于客观社会现实。思想家们清楚地看到,当世非但已不是恢复井田制的时代,更为重要的是与中唐以前相比,原有官田亦大量民田化,或出租经营如民田。土地买卖更为频繁,土地所有权转移加速,土地集中更为严重,土地私有化已为大势所趋,无可挽回。而且“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已经成为宋朝处理土地关系的基本原则,私有土地急剧扩张和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与此相应,人们的观念亦发生转变。正如顾炎武所看到的那样,汉唐之世,大土地所有者被称为“豪民”“兼并之徒”,“谓之豪民,谓之兼并之徒,宋以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看作对朝廷利益的威胁。赵匡胤云:“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因此,贫富分化不仅成为无可避免的客观存在,而且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如众所知,历代恢复井田制的努力,尤其是思想界的倡导,一直持续未断。在不少人看来,井田制是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首选方案。可是到了宋代,开始有较多人提出放弃井田制之类脱离实际的想法,同时,倡导面对现实,建立切实的制度和政策来解决贫富不均问题。元代郑介夫是主张抑制豪强、缩小贫富差距的学者,但他亦清醒地认识到:“井田永不可复矣。民得自有其田而公卖之,官安得而禁制之?田既属民,乃欲夺富者之田以与无田之民,祸乱群兴,必然之理也。”明代刘定之(1410—1469)明确指出:“井田之不可复也,久矣;井田之不必问也,明矣。必欲复井田,是驱斯民于畚锸,而非惠以饱暖也;必欲问井田,是试诸生以笔墨,而非求其实用也。”其后,不仅“井田论”逐渐销声匿迹,且如下文所述,业佃关系成为讨论社会关系的基础。应该说,这种认识是宋以后社会变化的客观反映。
上述变化又必然导致以下后果:一方面,由于国家或者官府已经没有办法完全支配“天下”的资源、财富,故不再像唐以前那样有足够的能力解决甚至包揽贫民的生计问题;另一方面,贫富分化、土地兼并的加剧、商品经济的发达,造就了一批有产者,即富人。这些人的财富自给有余,换言之,他们有能力接济他人。叶适之所以将富人与小民的关系模式界定如前所述,就是因为“县官不幸而失养民之权,转归于富人”。或曰“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农夫资巨室之土,巨室资农夫之用,彼此自相资,有无自相恤,而官不与也,故曰官不养民”。欧阳守道说:“官司枵虚,既不自力以养贫民,则当使富家有乐奉公上之心,不可使贫民有疾视富家之迹。”贫富关系问题不是孤立的,它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本质上是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化相关联的,问题的根源在于产权即土地资源所有权的变化。
于是,有力之家、富户成为资助贫民、救济灾荒的重要力量,已远非过去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凌虐小民、为害地方、危及社会稳定的因素,从而成为应该加以抑制甚或坚决打击的对象。
检阅宋代及以后历朝史籍,不难发现,在救荒及济贫方面有两大现象值得关注。其一是富户通过出粮出资救荒和参与灾荒救济管理的记载多不胜数,表明他们在救荒济贫事务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二是宋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荒政指南性质的专书,即董煟《救荒活民书》。此后,一大批荒政指南、救荒思想著述陆续涌现。而劝分——劝谕富民出资出粮救荒成为必不可少的荒政对策或救荒思想内容。包括基层民众在内,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富户及其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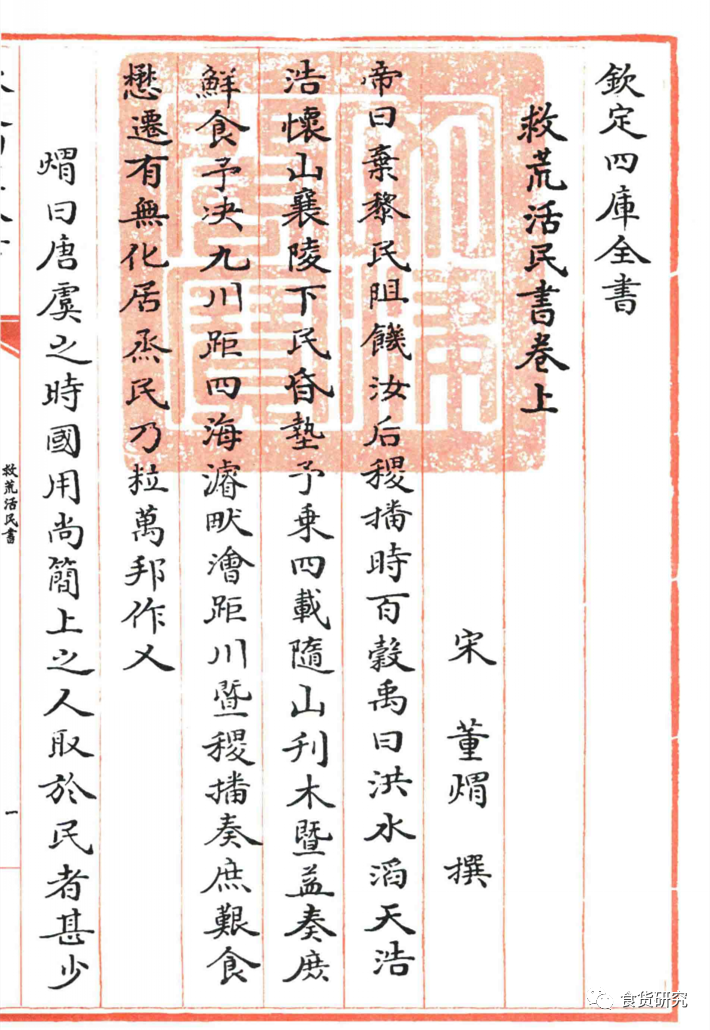
(宋)董煟《救荒活民书》
其三,论及造成贫富分化的原因,当然仍有人讲天命,如宋人程珌在《壬申富阳劝农》中写道:“大抵贫富、贵贱、死生、寿夭,莫不有命,命所赋受,毫发难逃。贫人当知分定,节食省衣,尽力耕桑,辛勤商贩。无萌负债之心,常思富人济我急用;勿萌偷窃他物之念,常思官法坏我肌体。富人则又自思曰:天之生财为众人用,今吾乃独多得焉,其可不知聚散之理乎?消息盈虚、天地阴阳所不能免,富贵其可恃哉!”清袁枚则云:“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民之有贫富,犹寿之有长短,造物亦无如何。先王因物付物,使之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而已。春秋时,阡陌未开,豪强未并,孔门弟子业已富者自富,贫者自贫,而圣人身为之师,亦不闻裒多益寡,损子贡以助颜渊,劝子华使养原宪者,何也?”历代论及者尚多,此不赘述。天命说的重点是要求贫富双方,尤其贫者一方要安分守己,不可有非分之想;富者则应富而好德,不可为富不仁。
但是,天命说之外,智愚、勤惰、俭奢被认为是导致富足或贫困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正如李觏所指出:“田皆可耕也,桑皆可蚕也,材皆可饬也,货皆可通也,独以是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兴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时、听上令也。”司马光(1019—1086)之说更强调智愚和意志因素:“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思远,宁劳筋苦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于人,故其家常有赢余,而不至狼狈也。贫者啙窳偷生,不为远虑,一醉之外,无复赢余,急则取债于人,积不能偿,至于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另外如叶适、王夫之、李雯等亦多从愚智、勤惰等方面理解贫富分化的成因问题。
明刘世教、吕坤(1536—1618)等人的看法有所不同。“且财非从地出也,铜山金穴,其始能亡掊克而致者鲜矣。是故吴越之间,一小豪起,而方数里之内,靡非其属厌之余也;一巨豪起,而方数十里之内,无不被之矣。满则必概,天道固然。兹固其全之之曰也。”“天下之财自有定数,我不富则人不贫,我愈富则人愈贫。”“天地之财,止有此数,富贵荣华既于我乎独偏,贫贱忧戚自于彼乎独苦。有余者之所弃余,乃不足者之所弃命也。”“不生富贵人,贫贱安得死!”这些论述,对财富分配不均及剥削因素的存在等问题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同时有劝谕富人应该救恤贫穷的目的。
其四,业佃关系成为集中体现贫富关系的主要形式。与土地私有、土地买卖、土地兼并相伴随,加之人口不断增长,尽管土地集中与土地分散互见,但土地资源短缺日趋显著,无地之家日多,租佃土地耕种渐成普遍现象,租佃关系也更发达。所谓“民无常产,有田之家,十不二三。今之耕者,率佃种他人田地,输租私室以偿公税者也”。对于土地兼并及租佃制度,欧阳修(1007—1072)曾抨击道:“今大率一户之田及百顷者,养客数十家。其间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过十余户。其余皆出产租而侨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佃户皆非富足而有蓄积者,遇水旱等自然灾害及婚丧大事即须向富户借贷,负担高息,结果“其场功朝毕而暮乏食”。苏洵的分析则更为具体、深刻。
贫富两个阶层通过业主与佃户这种形式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富者资贫者以为财,贫者恃富者以为命。其基本性质是二者相须方能成立。明清时期,许多地区的土地集中及相关问题更为严重。顾炎武(1613—1682)指出:“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毕并其税于田之中……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之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乞贷者。”前引朱熹、叶适、徐阶、唐鹤征、魏礼等人论及“上户有力之家”与“贫民下户”、“小民”与“富人”之间的关系时,无不将之和业主与佃户之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甚至相互重合,而贫富之间之所以有相须关系,佃田、佣工是其纽带。在许多场合,“有身家者”即等于地主,而贫乏或穷困者多属佃户。
当然,宋以后论者所谓富户、富民,已有不完全相同的内涵,或将富民加以区别。李觏有“富而强者”和富而不强的区分,董煟(?—1217)则将富民区别为“有田而富之民”和“无田而富之民”。“有田而富者,每岁输官,固借苗利,一遇饥馑,自能出其余以济佃客。至于无田而富者,平时射利浸渔百姓,缓急之际,可不出力斡旋以救饥民,为异时根本之地哉!”饥荒之时,无田而富的富民更应该出资出力救济饥民。李雯区别一般富民与权贵豪强,后者凭借特权致富而非靠勤力致富,具有侵夺性质。“苟非权贵之家,豪横相夺,其他勤力而广亩者不可谓侵牟也。”所应抑制者,主要是靠侵夺致富的权豪富户。但是,从救荒济贫的意义上讲,无论何种途径致富之富户,都起着重要作用,应该加以保护。明人顾起元辑时人有关富户、富人的主张为一则《三宜恤》,表达了对各种类型富户社会作用的充分肯定及相应的保护富民观点。顾氏认为:“三先生之言,皆深思远虑,与浮见者不同,因表而出之,以谂于当事者。”其说如下:
南都徭役繁重,所以困吾百姓者多矣。近年当事者加意铲除,始稍有苏息之望。向有议裁寄庄户之兼并,禁质铺之罔利,与搜富户之非法者,其说固亦有见第。余尝闻姚太守叙卿之言曰:“均赋者,不宜苛摘寄庄户,寄庄户乃无田者之父母也。令寄庄户冒役太重,势必不肯多置田,彼小民之无立锥者,安所倚命乎?寄庄户以田一亩予佃户种,必以牛与车予之,又以房居之。计一岁所入,亩之中上者可收谷二石,以其半输之田主,而佃户已得一亩之入矣。是寄庄户不惟无害于民,且有利于民,即田连阡陌,其仰给者不啻众也,何以尤其兼并也。”方司徒采山之言曰:“质铺未可议逐也,小民旦夕有缓急,上既不能赉之,其邻里乡党能助一臂力者,几何人哉!当僒迫之中,随其家之所有,抱而趣质焉,可以立办,可以亡求人。则质铺者穷民之筦库也,可无议逐矣。”王太守元简之言曰:“往日海中丞在吴中,贫民有告富家者,必严法处之。一时刁讦四起,富户之破亡者甚众,此大非。是邑有富民,小户依以衣食者必夥,时值水旱,劝借赈贷,须此辈以济缓急。虽一村有一富者,近村田房不免多为所有,然必是贫者方卖,卖于他人与卖于富家一也。且富家自非豪恶闵不畏法者,岂必尽谋占而计取之?假令摧剥富民,富者必贫,阖百千万室而皆赤贫,岂能长保?
最后,诸家论述中表现出显著的中庸即保富与恤贫二者兼顾倾向,并不绝对顾此失彼。宋以前,不少思想家把富人视为有害于社会稳定、需要加以抑制的对象,以致民间很早就有“富则多事”“温饱之家,众怨所归”之类的说法。与此相应,均平贫富、抑富右贫、抑强扶弱甚至锄富恤贫的社会控制主张颇为常见,均田、限田等对策则不止一次见之于改革实践。因此,就在肯定富户地位、作用,保护富户的议论愈益增多的情况下,完全相对立的观点依然不断。即使到了明清时期,此类主张仍屡见于朝野议论。至于灾荒时期富户接济贫户更是应该之事。著名的救荒思想家董煟认为富人有责任、义务赈济穷人。“有田而富之民”遇到饥馑时,出其余以济佃客乃天经地义之事;“无田而富之民”更应该在饥荒时出力斡旋以救饥民。明徐三重《采芹录》卷1指出:“限田一事,均产平役,节富右贫,最为治安善政。昔人每苦救荒之策无奇,窃谓荒策亦孰奇于此……自阡陌既开,田无常制,多者吞并至千万,无者不得置锥。于是始有奴婢、佃户,而贵贱、有余不足,大悬殊矣。丰稔之年,贫者力作以养富,凶歉之岁,富者厚自畜而困贫,此三代以下至今日弊政,天下所由不均不平者,胥是也。夫言井田于郡县之日,非迂则妄,然富贫何不可均量也。”徐氏以均贫富为救荒之根本,有一定的代表性。明俞汝为《荒政要览》载:“贫富相周,有无相济,此邻里之义也……若有擅富要利,坐视民饥不与平籴者,是为奸民之首,里老举呈,饥民告发,官发银两尽籴运上仓,仍问重罪不贷。”“若富豪恃强挟逼赈济银两以偿私债者,饥民鸣告,将恃强之徒用八十斤重枷枷号,从重问罪。仍加倍追给银补饥民。凡民间私债,俱候年丰,渐以理还。”带有显著抑富倾向的事例甚多。正统年间,礼部尚书刘定之更公开提出“锄富恤贫”的主张。
海瑞(1514—1587)是明清时期地方官中力主抑富右贫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剥夺富人多余田产以与贫人,推行井田制,目的是“田井而贫者得免奴佃富家之苦”。又主张按资产派徭役。富者宜当重差,当银差;贫者宜当轻差,当力差。田多者重,田少者轻。论及荒年贫富关系,海瑞的抑富倾向亦颇明显。首先,他要求业户量减额租。“今年水灾,富家欲照往例取租,佃户称无收拖赖。臣令之酌量灾数,二家均认。”其次,禁止富户发饥荒之财。“今本县细访得各都图富积谷粟之家,每每乘荒岁勒掯贫民,质物典当,倍约利息,其贫甚虑无可偿者,虽倍约亦固吝不与。”因此,他令富户“量将所积米粟借贷贫民,不许取利……如仍前略无恻隐,倍称取利,许贫民指告,以凭重治”。不能说海瑞之主张已为明代绝唱,但至少有大量史实证明推行其说的成效不佳,而且难以持续。至于清代张伯行之例,已见前述。

(明)周臣《流民图》局部
一方面,主张保护富人利益却不忘记加以限制。限制富人的出发点有二:一是从朝廷统治出发,不允许富者力量过于强大,尤其豪强势力不可无限制地发展;二是从稳定社会秩序着想,缩小贫富差距,平衡贫富关系,减少社会冲突。其最终目的并无二致。另一方面,主张保富的思想家亦没有完全忽视恤贫。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是主张保富的同时不忘恤贫,甚至强调为恤贫而保富;二是保富并非绝对的、无条件的。条件是富民不能为富不仁,而应该有恻隐之心,甚至有仁爱之心,救恤贫民。简言之,应该保的是“富而好德”之富,而非“为富不仁”之富。均平、中庸乃至抑富右贫等思想观念在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传统,在传统社会控制思想中长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可能轻易退出思想领域,因此,在救荒问题上不时有所体现并不奇怪。

